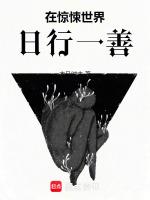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春山似薇全文免费阅读 > 第150章(第1页)
第150章(第1页)
“可是对不起,我太懦弱了,我没法原谅我自己,我只能把这份罪责转嫁到你身上。春山哥哥你听明白了吗,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不愿意带你去见妈妈,我是不敢。如果说过错不在你,那我就必须正视自己的过错,我不敢……”
钟似薇说得上气不接下气,眼泪明明不经喉管,却好像已经要将那里糊死了。
“我知道,似薇。”一只手抚上发端,纪春山用好不容易回复的一点力气,抱住怀里的女人:“我都知道,你的善良、恐惧、摇摆、冲动,我通通都知道,你这样好的人,又怎么会轻易原谅自己?”
他知道,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钟似薇睁大眼睛,震惊万分地听他讲。
“似薇,不管你是怎么想的,从现在起,放过自己好吗?你已经折磨自己足够久了,走出来吧,从前的一切就结束在这里吧,我们重新开始。”
他的声音很孱弱,却也因此格外温柔,温泉水一样,一寸一寸漫过她沾染寒霜的肌肤:“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叫纪春山。”
好。
重新开始。
无论是谁的错,无论是谁的牢,他跳下来了,就当替他们一同死过一回了。
前尘往事,既往不咎。
“你好,我叫钟似薇。”
纪春山歪了歪脑袋,往钟似薇脖颈处蹭了蹭,带着几分撒娇的得逞:“似薇,这一次,是我主动的。”
这一年的正月十五,纪春山和钟似薇一齐回到了凤城。
奔驰驶入宁安巷,昨日的世界又复重现。这么多年,世界早已日新月异,这里却岿然不变。吊着两条大鼻涕的孩童,三三两两玩着卡片牌,女人穿着毛毛鞋出来倒垃圾,随口就要跟邻居对骂几句,男人们抽商店里的最便宜的烟,喝52°最烈的二锅头。
见到有生人进来,都会停住脚步看一会,确认没什么好看的,才斜着眼嗤一口气去干自己的事。老的不能再老,破的不能再破的出租屋里,住的人早换了好几茬,生活习性却一丝不茍地保存了下来。
纪春山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的是一对老夫妻,快六十了,据说是因病返贫,丧失劳动力又没有退休金,不得不搬来这里度日,平时靠收点废品过活,为此家门口堆满了废纸皮、易拉罐。
钟似薇住的那套两居室,现在挤了一家四口,父母是外地前来务工的,一儿一女就在这附近的小学读书。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巷子里的人都隐隐敬佩这对夫妻,因为即便如此,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成为留守儿童。
没什么认识的人了,除了李卫国一家。
李卫国老几百年前就是“痨病鬼”,看着要死不活的样子,居然超长续航到了今天。正午时分,他脚下放着个小筐,坐在门口剥蒜。一见那辆奔驰驶进来,就抻长了脖子去看。
他一眼就认出了车上下来的人。
“你不是那谁谁谁……俞美莲的儿子,对吧?小姑娘叫什么薇来着我忘了,紫薇?”
钟似薇笑了笑:“李叔,我是似薇,这是春山。”
“哦对,似薇,春山,都好些年没见了,看起来发达了呀,恭喜恭喜,今天怎么有空回来了?”
时间真是个神奇的法宝,无论当年相处得多么龃龉,历经年岁,都会因为时间的滤镜而成为珍贵的故人。旧时人,旧时物,共同铸就了我们的来时路。
李卫国很热情,说什么都要请纪春山和钟似薇去家里吃饭,被拒绝后,又坚持要让人进屋喝杯茶。饭可以不吃,茶是不好不喝的,两人不再拒绝,跟着他进了屋。
“桂兰,来客人了,看还认识不?”
李卫国对着厨房喊了一声,一个头顶花白的女人擦着手走出来,愣了愣,道:“这不是春山和似薇吗?似薇,今天正月十五,你是回来看你妈妈的吗?”
不知为什么,钟似薇蓦地鼻尖一酸。
“李姨,好久不见。”钟似薇记得这个叫桂兰的女人,相比于在巷子里出尽风头的李卫国,她是个很安静很规矩的女人,原先在玩具厂上班,总是一大早骑着单车出门,天黑了才骑单车回来。
印象中她跟妈妈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只是偶尔碰见了寒暄几句,各自聊聊工作和孩子。却原来这么些年,在这条早被全世界遗忘的巷子里,还有人记得妈妈的忌日。
李桂兰给客人倒了茶,又从柜子里翻出过年招待客人剩下的瓜子和糖果,用大红色的塑料盘子装着递上来,而后又复钻进了厨房——他们的孩子在附近汽修店上班,一会该回来吃饭了。
李卫国兴致很高,老些年没见到熟人了,即便是之前没怎么打过招呼的晚辈,也总想聊点往事。
可惜这些往事总碰着壁。
他问俞美莲怎么样了,纪春山说去美国了,李卫国登时双眼放光,说那你怎么不跟着一起去?气氛马上怪异起来,纪春山只好笑笑说自己吃不惯西餐。
过一会他又问钟似薇,怎么这些年回凤城扫墓,都不来宁安巷看看,钟似薇也只是笑,她没法说这里装着她太多过去,沉重得像一个装满煤气的罐子,她不敢揭开也不敢靠近。
李卫国碰了壁,便不再问他们,只聊自己的事,说孩子在汽修店上班,找了个对象是外省的,人很能干,就是眼睛有点问题,斜视。
又如数家珍地掰数着,哪一户是什么时候搬走的,哪一户又是什么时候搬来的,他活成了宁安巷的守巷人,宁安巷的事,他都知道。
“走的走,来的来,那时候的朋友,就剩我们这一户了。”李卫国说到最后有点伤感,扯着嗓子往里头喊了一句:“中午有菜不,搞点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