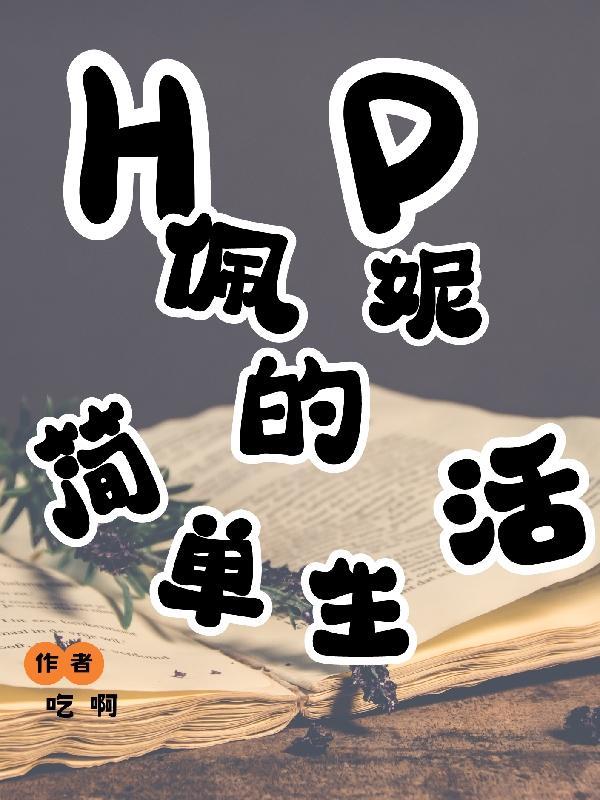笔趣小说>童养媳穿越文 > 第三十三章(第2页)
第三十三章(第2页)
“少爷……”翠红讪讪走过来倒茶,蒋煦脸色稍稍暗,缓慢接了茶杯,目色却是动不动盯着翠红,翠红抬头对上,不由得心头起伏阵凛意,暗叫不好。
蒋煦品了口,不轻不重道:“翠红,茶凉了。”
翠红执拗不走,面是担心蒋煦对方沉碧有什么不规矩,面又着实是怕着阴阳怪气儿蒋煦:“,去换热茶来。”
蒋煦见翠红光说不动,不由得笑出声来:“去啊,怎么不走,家小姐在屋子里还能丢了胳膊少了腿儿不成,怕个什么?”
方沉碧见势怕蒋煦又拿翠红使气,忙支使翠红道:“且先下去换茶来,愣在这里做什么。”
翠红犹豫了再三,终还是端着茶壶先出去了,等着人走了,蒋煦又靠过来,脑袋探过方沉碧肩膀,带过股子苦森森药汤味道,他软软念,听得方沉碧骨子里头钻了虫样浑身跟着冷。
“没多少日子就满十五了,等着及笄,就要过了门儿。”
方沉碧微微垂目,往前又挪了挪身子,勉强与身后蒋煦分开微细点距离,含糊应着,身子绷得笔直。
“怕?”蒋煦再往前靠过去,再不是隐约擦过后背,而是密密实实贴了上去,方沉碧晃猛地往前躲,这急竟推响了面前那张桌子。
“少爷……”
蒋煦见反应,心下里又是恼意又是得意,也说不清究竟是怎么样畅快。且先不说方沉碧是不是他心里头喜欢女人,但说这孩子几年光景竟是愈漂亮出挑,只要是个男人见了,心里也会跟着长草儿,谁也不厌烦美人儿总是这个理儿。
况是这丫头近几年跟着他娘身边学着,再不是宝珠这种心高眼低又不懂识得抬举粗人能比,犹是他娘跟他私下里通过话来说,方沉碧是个能人,能帮他操持这个蒋府,也能是他成了当家得力助手,这样女人本就少得,还又托生成了个标致美人儿,他岂有不要之理?
蒋煦从方沉碧身后探过手臂,紧紧圈牢了身子,虽说也是常年卧病在床人,可真正角起力来也绝不比介女子差。方沉碧又不敢大力挣扎,唯恐蒋煦得了闪失自己也不得好过。扭了扭身子,蒋煦便抱得更紧,那张尖牙利齿嘴在耳朵边细细道:“就算不等及笄,现下要了也无妨,终究都是屋子里头人,早晚有何区别。”
方沉碧急道:“女儿嫁人本都是如此规矩,少爷现下破了规矩让沉碧在府里也很难抬头做人,况是天下没有不透风墙,总有人嚼舌头。不如少爷再等等,下个月便及笄,少爷若是真想要,便正大光明迎进门便是,也容风风光光嫁了回人,心里头甜着。”
蒋煦闻言笑出了声,仍不收手,只道是束牢了方沉碧身子朝桌子压了过去:“现下也没得别人在,容得了些甜头权当是这么多年忍着让着利息份了。”
方沉碧哪里愿意,见蒋煦愈大胆起来,便拼了命挣扎。
蒋煦到底是个成年男人,又早就尝过男欢女爱甜头,只道是动作熟练将手顺着方沉碧衣襟伸了进去,夏日本是闷热,可蒋煦手却是凉丝丝,顺着方沉碧腰身直往上摸,划过脊梁也蹭过背上伤口,激得方沉碧下意识加大挣扎起来。
“放手……”
现下光景,由着方沉碧喊出什么都是白费,蒋煦完全是鬼迷了心窍,尝不到甜头,那肯罢休?到底是水般人儿,那皮肤跟剥了皮儿荔枝果子样,滑嫩嫩细腻腻,只嫌还是略有瘦弱,皮肉虽上好,但仍旧骨感,他甚至可以摸出脊梁骨节走向。
昔日床第之间他也让宝珠脱得精光,而后顺着脚腕直往上摩挲,划过大腿,肚腹,胸脯,颈项,他犹是喜欢从宝珠肥臀摸上背后,因着宝珠本就丰腴,摸起来时候好似摸着块豆腐般,满手颤颤肉感,线条凹凸有致很是有感觉。
可到底女人与女人是不同,丰腴身条再好,摸多了也就腻歪了,况是蒋煦本就单薄,倒也不那么喜欢比自己还要有肉宝珠,偏是宝珠又可以上赶子,方才摸了两下就叫个不停,他也厌烦,只觉得这女人太过作假了些。
现下干瘦手指下是具青春玲珑身体,皮肤相触那瞬间,就似自己年岁也跟着往回去了好几年,曾经年少时候冲动新鲜劲儿又如数回了来,蒋煦兴奋是前所未有,也是宝珠给不了也达不到。
凭着那股子强烈欲望从心头迸,蒋煦也不愿收着敛着,只想快些吃到嘴里才算个定数,爱不爱方沉碧他不管,他只要得到,得到个女人身体,进而得到心,征服便容易太多了。
方沉碧根本挣不脱,也不管后背伤还疼着,拼命往外挣。其实道理都懂,只是在这瞬间还不能接受蒋煦,明媒正娶也非愿意,那么私下里投机摸狗就更是嫌龌龊了。又不得喊大声,便是叫来了人也无济于事,只会让自己脸面尽失,等着大夫人知道了,肯定也是要骂要罚。
“少爷,放手……”
蒋煦脸有些扭曲,似乎脱了自己控制般,愈疯狂按住方沉碧肩膀,另只手从后背绕到前面狠狠按住肚腹,颤抖摩挲并大口喘气起来。
纤细腰,绷紧小腹,每寸皮肤都在燃烧,从蒋煦手直烧到了他丹田,火势不可收拾,已是极快蔓延到他全身,他不知所以,只是跟着身体本能去做,那双薄唇含住了方沉碧珠贝般耳垂,那粗气从他喉头跃出他口,沙哑不像话。
a无限好文,尽在晋江文学城
“别扭着性子,由着要了,早些怀了孩子有着好日子过不尽。”
方沉碧已是历尽全身气力挣扎,蒋煦却是被情欲控制了全身,两人奋尽气力角力,方沉碧每贴近他动作都似在燎原大火上又加了道,蒋煦本就有着滑精毛病,犹是愈激动就越容易泄了,他感到小腹绷得仿若断了肠子般,浑身神经也瞬间跟着揪成把,仿若脚下也跟着轻了,身子玄然欲飘。
他绷不住,提气松,到底是由着那股子精血就这么出了来,身子虚,不禁闪了神儿,泄了气儿,浑身没劲儿。
衬着蒋煦这闪神,方沉碧拼了命往旁边逃,蒋煦遂失了手,身子又虚,却也很快堵住方沉碧去处,喘息急很,张脸不是个颜色,阴鸷道:“方沉碧能躲到何处去?方家家子老小都巴望着给钱给物养活着,马文德还指望给他出人头地给他养老送终,就算这些都不顾着,放走,还能走到什么地方去?安生出了蒋府嫁人生子过日子?还是由着府里头谁给撑腰壮胆,从府外头给聘个当家去?
等着走,又有多少人因着受牵连,跑不掉那些平日跟在身边或是伺候丫头婆子,死罪免了,活罪可有们好受。就是要看着造孽非得由别人待还,或是将来也死在手里,说还怎么当跟不相关过日子去?”
蒋煦越说越是兴奋,只管是笑不可支指了指方沉碧:“啊,说是剔透玲珑性子怎看不透这花样里头九曲十弯了,道是娘平日对欢喜,可怎不知晓最想让进着屋子里头人也是老人家呢。不管今儿是磕死在这屋子里头,还是削了头做姑子去,都饶不得和方家,娘也样不会。活着,是这院子里头妾,是死了不过是荒野上座孤坟,就算给立碑也要冠上姓,方沉碧,道是还躲什么,还逃个什么劲儿?”
说道尽兴之处,蒋煦还不忘把陈年旧事掏出来过把嘴瘾,格外矫情道:“或者是指望着悦然从京城回来把带走?果真好笑,那小子攀了京城富李家,自是想着怎么娶了李家闺女续他辈子富贵,他在蒋府再不如从前受器重,这掌家位置也悬了,道是他个肩不能抗手不能挑少爷身份,除了攀附别人才好过好日子,他还能做什么选择?跟去耕田纺布?吃糠咽菜?哈哈,那也太过蠢顿,将来失望倒霉也是活该,活该不知好歹。再者说方沉碧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不过是他年幼时候玩伴儿还说不上,倒是还有痴心妄想资格吗?”
方沉碧听着蒋煦这句句话,心头上不是委屈,不是幽怨,更不是恼怒,而是彻彻底底平静下来了。蒋煦嘴是照旧刁钻刻薄,可道理说得却是无比通透详尽,他诚实而残忍,竟没句言过其实威胁。
懂,直都懂,就算方安不是留在这里缘由,马文德不是,翠红马婆子也不是,仍旧逃不开,便是舍弃切,不管不顾自私逃避时候,蒋家对钳制也不会消失,不过是从间接转为直接,了不起弄死只当是可惜了培养这么多年,说到底也没多大了不起。
而在这个世道上,主子要了奴婢命,也是稀疏平常事,哪会有人替鸣不平讨个正义去,就算蒋府人不要小命,由着名声坏尽,方家受制,等到落难之时,谁人肯伸手帮把说不肯定,许是到时候什么都有可能,落到最后也不过是自己活不下去,沦落风尘卖身讨活,那便是真真辈子都完了,还不如现下委屈着。
定定神,方沉碧去淡淡道:“倒也没想到少爷想这么多,只顾着平素脸皮薄了些,也不爱给下人留着话儿把嚼得心烦罢了,既然少爷这么多年都等得,也知晓便是生出七头八手来也逃不过少爷手掌心儿,那更不用急于时,让日后总为着这事跟别人烦着,倘若他日人家冲着说几句难听来,可是连句反口话都说不得,也不爱憋着自己性子难受来着。”
蒋煦听了这话笑了笑:“原是这道理都懂,想也正,便信了。”说罢有些腿颤又昏沉,自己扶了床柱坐了下去,阖了眼倚在床边,又朝方沉碧道:“与说,这次爹病重,悦然定会回来,他为着什么应该知道,而又是什么身份也清楚,到底谁是谁身后人儿,该办什么身份儿事,也不用教。若是让悦然掌了家,只道是日后享福不是,更不会是,只会是别家女儿做主,可服气?”
方沉碧明白蒋煦话里话外意思,应道:“沉碧懂了。”
蒋煦弯了嘴角:“很好。”复又道:“既然懂了,就来帮换身儿新裤子。”
方沉碧平了平心,走过去跪在床边帮蒋煦脱下弄脏裤子,男人身体也不陌生,只是现下见了蒋煦只觉得心口里泛着恶心,和着那股子腥膻味道,让不得不屏住呼吸,将裤子随手团成团仍在床脚,再不看眼。
蒋煦下身裹了薄被子躺在床上等着,方沉碧又利落打了温水亲自帮蒋煦擦拭干净,再换上套新。
总在不停思索,这就是日后丈夫,要伺候他辈子,为他生儿育女,并且再无任何抉择可选,这不是恐惧,而是彻彻底底陌生,就像是隔着辈子活着,碰不见,看不清,也不愿意靠近,不愿意了解,辈子就这么赤裸而凄凉展现在眼前,是种落到池底不由再见天日彻底妥协和看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