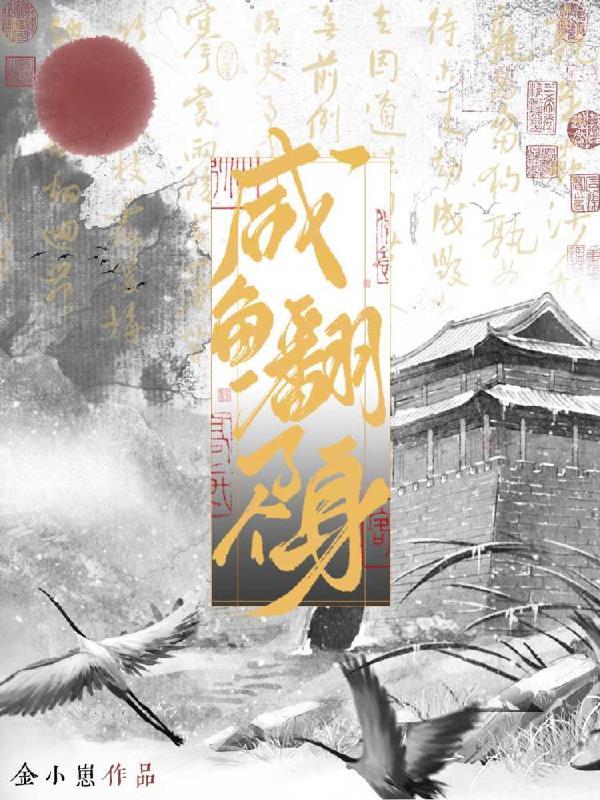笔趣小说>见字如面写信开头如何写 > 第38章(第1页)
第38章(第1页)
我抬起头看她,说不定正是因为儿时的遭遇才让费一宁这么希望拥有一个安稳的生活环境,似乎一切有迹可循,当年不知不觉种下的因,结出了今日的果。
翻弄着一沓废纸,里头夹着几张显眼的体检报告,上面是我自己的名字,忆起上初中的时候我妈检查出癌症,当时只觉得天都要塌了,我要变成没妈的孩子了,我清晰记得那天傍晚来接我的不是我妈,也不是我爸,而是我爷爷蹬着二八大杠。
然后我妈我爸就从我生活中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时候不清楚他们为什么要去别的城市看病,在那个懵懂的年纪,我以为癌症就等于死亡,每次给我妈打电话都当成最后一次。
这么想的话我当年种下了什么因,才结出了今日林树的果呢?
费一宁走到我跟前看了看我手里拿着的东西,“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还纳闷儿,小小年纪这么惜命的吗?每年都不落下,阿姨现在好些了吗?”
我点了点头,“比我体格还硬实,去爬山比我走得都快。”
没说出口的是那时候我妈的确鬼门关里走了一遭,而把她从阎王爷手里夺下来的不仅有医生和她自己的顽强毅力,还有我爸,确诊到回家从头到尾我爸都没假手于人,日夜不离陪着她,以至于我妈后来自己在家每天要给上班的我爸打三四个电话,要我说是家里苍蝇在窗上打个刺溜滑她都得跟我爸说一声。
所以我妈跟阎王打了照面之后我的生活就又一切恢复如常,回头想想,我的人生好像一直是这样,虽然偶有波澜,但有惊无险,终究还是在那一小方格子里规规矩矩,也挺好,我经不起折腾。
“那你和林树实习打算去哪?”费一宁掐腰站在宿舍中央。
我回头一瞥,“没问过他。”直起腰想了一下,“要么沈阳,要么大连,我都无所谓。”
话音落,桌子上的手机嗡嗡震动两下,我正伸手去拿,她刻意踮起脚看了看跟着起哄,“呦呦呦,真不经念叨,说说还来了,我看看是不是林树,不是他我转头就去打小报告。”
“是不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一说完,费一宁嘿嘿嘿笑个不停,双手搂上我的腰,“哪儿能呢?林树找你干嘛?”
“约会。”我故作神秘锁上手机屏幕。
她捏着嗓子故意用又尖又细的声音重复一遍我的话:“哟~约会~”
初秋时热气还没有驱散,我瞧着天边霞光将火烧云映衬得像是一片玫瑰花海,两步走向窗台,透过玻璃瞧见花坛边上正站着一个熟悉人影,白色衬衫,浅色直筒牛仔裤,与初见时一模一样。
“林树!”我打开窗兴奋向他挥了挥手,像是困在笼中的鸟儿窥见了自由,不过这自由无关身体,而在于精神。
他转过身的这一刻,我见到了这世上最美的风景。
林树捧着一大捧牛皮纸包好的茉莉花,面颊被晚霞映得红红,笑容依旧,我怀着爱意与他对视,区区几秒远胜春花秋月。
只是这花束看着有些古怪,我目光停留了一会儿,不过管它呢。
“等我!”我隔着防盗窗大声喊,然后无视费一宁的调笑飞奔出去。
他像是掐着时间迈步,我绕过长长走廊,站在宿舍楼大厅时刚好看见他站在门口,我迫不及待一个箭步冲到他面前去,只觉得见了他浑身都暖洋洋。
“给我的?”
“嗯。”他的眼睛亮晶晶看着我,毫不犹豫点下头,却又匆匆从包里翻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东西来,塞进我的怀里,“不是鲜切花,有根的,你可以把它栽进花盆里,就当弥补一下今年夏天你失去的那盆茉莉。”
我将那报纸微微扯开一角,里头是个很简单的白色陶瓷盆,疑惑看他,“什么意思?”
“涝死的那一盆,这回下雨前要记得收回来。”林树扶着我的双肩,轻轻将我推进宿舍楼,“回去换衣裳,我在门外等你,一起去吃饭。”
而我却还呆呆傻傻想着他的回答,之前只是随口一说,以为他会随便一听,遂拦下他的手,认真看着他,“林树,我想知道这样你累吗?”
他似乎有些意外,目光在我的脸上寻着有用的线索,“累?”
“好像我无论说什么你都能记住,可是我却什么都记不住……”我低头看向茉莉花油绿的叶子,声音越来越小,甚至在心里开始替他感到不公平。
林树愣了半晌,许是摸不清我的脑回路,想明白后淡淡笑着,指引我看向天边的落日,那一抹火红余晖就要散去,金红金红的太阳一半已经没入地平线。
“看到了吗?”他柔声问。
我点了点头。
“喜欢吗?”
我继续点头。
“那我们就只要夕阳好不好?”
我点头又摇头。
“为什么不好?”他低头看我。
“喜欢但留不住,我控制不了太阳。”
“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想你、念你。”
我转头,他弯腰。
我惊讶睁大了眼睛,他却深情闭上了双眼。
一抹温热覆上,好似那天边的火烧云落在了我的双唇,我措手不及向后退了几步,倘若不是林树拉住我,说不定要撞在寝室楼的大门上。
ok,抵抗无效,全线溃提,我吻到了火烧云,心中小鸟仿佛在天地间肆意撒起了欢儿。
直到他撤离,我才壮着胆子扭捏低语:“好多人看着呢。”
“要不……我跟她们道个歉?”他假装认真,等话说完面上一副无辜表情。
“我换衣服去了。”拖着脚步转身往寝室走去,满脑子都是林树方才说的话,一遍一遍又一遍,那感觉到像是小时候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小猫小狗,爱不释手,非要抱在怀里反复摸个不停,又或是得了什么觊觎已久却不常吃到的零食小吃,哪怕是包装纸都不轻易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