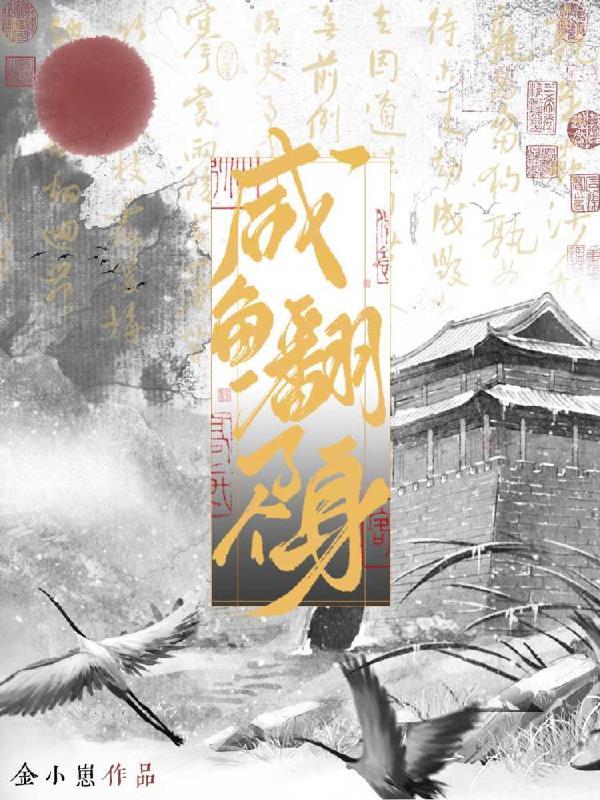笔趣小说>让他哭全全文 > 第119章(第2页)
第119章(第2页)
肖厌皱眉,认真地确认着重新见到姜晚橘至今是不是一场虚妄大梦,侧眸就看见了俯在床边的女人。
柜头亮着盏小灯,姜晚橘牵着他的手,正闭眼在睡,这姿势舒服不到哪里。
那点茫然陡然落下,就像先前说的那句烂俗的情话,凌晨三点半,他见了他的小太阳。
肖厌看了许久,呼吸轻轻,反握的力道不重。
但陪在身边的人还是睁开了眼。
姜晚橘抬头对上他那双沉而深的眼,默了半晌,惺忪迷蒙里回神:
“你醒了?”
肖厌鼻音低沉,“嗯”了一声。
姜晚橘坐起来一些:
“脑子也醒了?”
肖厌:“嗯?”
“你就好像那大傻逼,怎么想的烧成那样了还冲进去。”
她出口就是一句不好听的,肖厌顿顿,哑笑回:
“这就是你对伤员的态度。”
姜晚橘:“有意见吗。”
肖厌:“没有,你说什么是什么。”
姜晚橘显然吃软不吃硬,男人一放软态度,她就哑了炮,一时半会儿不知说什么。
前一夜肖厌是躺救护车来的这里。
当时他一身的伤,大火并没有因为他长得好看或者钱多就仁慈几分。
往日一丝不茍矜贵的男人满身狼狈,黑发混乱,白衬衣都要被烟染成灰的。
姜晚橘看在眼里,心疼难免。
房间里安静,肖厌接了刚才那句骂他的问话。
肖厌:“万一你真的在里面。进去了出不来还能给你做个伴。”
是个比较长的句子,他现在的状态说起来有些吃力。因为语气轻描淡写,听来飘飘然没分量。
姜晚橘知道,他底下的情绪只重不清。
聪明人做冲动蠢事时,都带点破釜沉舟的味道。
追根溯源,是太在意。
她回:“真爱我,心甘情愿殉情,命都不要了。”
肖厌哑着嗓子散漫道:“是,我恋爱脑。”
姜晚橘:“看出来了。”
冬天气温低,医院里本就不是什么暖和地,半夜到处都冷。
姜晚橘坐了前半夜,手脚难免冻僵。
肖厌一只手挂水,一只手牵着她,随后挂水的手拉起白色被子,牵她的手收了收力。
病房里安静,这一套动作意思明显,八九不离十邀她共享被窝。
姜晚橘看他的眼。明知故问了一句:“干什么。”
肖厌开门见山:“一起睡个素的。”
姜晚橘:“你看看这病床大小,躺你一个身长腿长的差不多了,还硬要我来挤。”
肖厌瞄一眼她因为冷微微泛红的指节,拐着弯给出四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