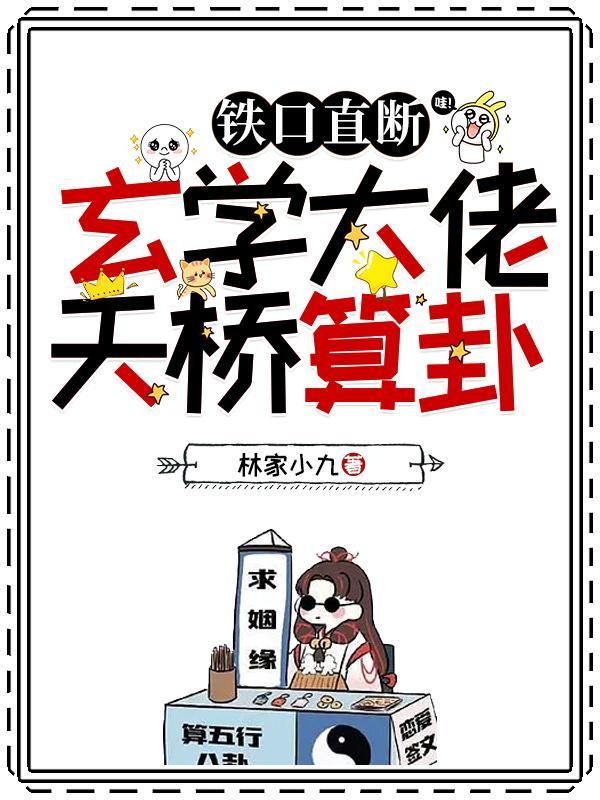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故事罗伯特麦基 > PART 1 人物礼赞(第3页)
PART 1 人物礼赞(第3页)
在第五章,我们将探讨内在人物的写作,这是一个如何将你的内在生活转化为人物内在生活的技巧,于是乎你的人物便变成了你认识的人,你知她犹如知己。[13]
结语
写得糟糕的人物能向我们表明其他人不是谁#pageNote#6;陈词滥调的人物能向我们表明其他人更喜欢谁;独一的人物能向我们表明我们更喜欢谁;移情人物能向我们表明我们是谁。
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允许我们去实现危险的满足,如复仇,所以我们会饕餮于故事的愉悦满足。我们召唤故事来将我们运送到无数个不同的世界,但能将我们带到凡人境界之外的司机则是人物,而驱动着我们这种想象之旅的燃料便是移情。
千百年文学虚构所提供的复杂人物的多样性远远超越了我们一辈子所能遇到的真人的范畴,并且丰富了我们对所遇之人的见解。而且,由于我们
对人物比对真人更加了解,所以我们对他们的那种爱便很少施于真人。当然,我们从一开始便对真人不太了解,哪怕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人,所以这一点也就不足为奇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如果你并不觉得虚构的会优于实际的,那么你可能要重新考虑你的职业选择了。
第二章
亚里士多德辩题——情节vs人物
“情节驱动”和“人物驱动”这样的术语由影评人在二十世纪中期发明,以标志好莱坞影片与欧洲电影的区别——抑或其视野中的大众娱乐与高端艺术之别。随后不久,书评人也开始依葫芦画瓢地以此来评说严肃文学和畅销小说的分野。外百老汇原本有百老汇检验场的功效,但在1960年代,纽约的戏剧界便沿着四十二街画出了一道艺术与金钱之间的分界线。这一型制亦被英国戏剧复制,伦敦西区的传统舞台与周边的先锋派形成区隔。多年之后,美国电视也分为订阅节目与广告资助节目,使得流媒体为成人观众而创作的人物驱动艺术与商业电视网为家庭观众而制作的情节驱动娱乐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亚里士多德的排序
这种分野古已有之。在其《诗学》中,亚里士多德对戏剧艺术的六个构件,根据其创作难度和对作品的权重,进行了从高到低的排序:(1)情节;(2)人物;(3)意义;(4
)对白;(5)音乐;(6)奇观。
他相信,比之人物,事件的创作需要更大的艺术匠心,并能以更大的力度打动观众。他的金科玉律统领了两千年,但从《堂吉诃德》开始,小说进化为统领性的故事讲述媒介,而且到了十九世纪末,作家对写作的认知便颠覆了亚里士多德清单的前两项,宣称读者真正想要的是刻骨铭心的人物。他们主张,情节的事件线只不过是作家展现其人物的晾衣绳。
这一理论认为情节是物理位面和社会位面上的作用与反作用,而将人物限定于意识和潜意识范畴的思想和情感。事实上,这四个场域是互相影响的。
当一个人物目睹一个事件,他的知觉便会立即将其传导到他的脑海,于是乎该事件便会在他的外部世界发生的几乎同一瞬间发生于他的内心。反之亦然:当一个人物做出一个决定,这一内在事件便会随着他将其付诸行动而变成外在的。外在事件和内在事件通过知觉而在不同层面自由流淌,从内到外,由表及里,循环往复,互相影响。将情节的定义限定于外部行动便漏掉了人类生活中所发生的绝大部分内容。情节驱动vs人物驱动之辩便是似是而非的诡辩,而且自从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的榜单以来便一直都是。
质问情节和人物到底哪一个更难创作,哪一个更有审美意义,便是犯了一个范畴错误。
询问二者到底谁多谁少、谁强谁弱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同一的:情节即人物,人物即情节。二者是同一枚故事硬币的正反两面。
一个角色直到一个事件将其行动和反应激活之后才能变成一个人物;一个事变直到一个人物导致和或经历了其变迁之后才能成为一个故事事件。一个未被事件触动的人只不过是一个独立的、没有生活的、静态的肖像而已,其最好的归宿是挂在墙上。一个没有人物的活动就像是大海上的一个下雨天——一个重复琐碎、毫无相关性的非事件。为了深入了解这一区别,我们需要定义术语。
人物、情节、事件
人物指称的是一个虚构生物,他要么导致事件发生,要么在他人或他事导致事件发生后做出反应,要么二者兼有。
情节指称的是故事对事件的安排。因此,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是不存在的。堪称故事者,必须有一个事件型制,亦称情节;堪称情节者,则必须将事件铺陈为一个型制,亦称故事。无论故事多么简略,所有的故事讲述人都要将发生在人物身上的事件编织为情节,并据此而设计事件。
由于一部虚构作品是透过时间来进行演绎的,其讲述形式便可以变幻无穷,并与经典形式背道而驰:视点转换,直奔主题的事件堆砌,因果有序地事件进展,故事套故事,闪回,重复,省略,可信
情节,奇幻情节——一切皆取决于如何才能最好地表达作家的视觉。但是,无论一个故事的事件设计如何挑逗好奇心,读者和观众最终都只会锚定于通过人物而进行的故事讲述本身。
上述两个定义所共有的一个术语便是事件,所以咱们必须对其进行精准定义:词典对日常事件的释义是发生的事。然而,在故事中,如果一件发生的事没有任何价值变化,该事件便毫无意义。例如,一阵微风吹过,对草地上的树叶进行了重新排列,事情的确发生了变化,但那一事件却毫无意义,因为它毫无价值。
对故事讲述人而言,价值被定义为人性经历的二元,其负荷可由正极变为负极,或由负极变为正极:生死、正义非正义、愉悦痛苦、自由奴役、善恶、亲昵冷漠、对错、意味深长毫无意义、人道非人道、团结不团结、美丑,如此等等。这一能给生活充电,使之发生意义重大的极化改变的二元清单事实上是无穷无尽的。因此,故事艺术通过在事件中灌注价值而赋予其意义。
例如,如果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的感情从爱(+)变成了恨(-),这一事件便变得有了意义,因为其爱恨的价值负荷#pageNote#7从正极变成了负极。或者反之,如果一个事件导致一个人物的财务状况从贫穷(-)摇身一变为富
有(+),这一改变便有了意义,因为贫困财富的价值负荷经历了从负极到正极的位移。
因此,一个故事事件便是一个人物生活中的一个价值负荷的瞬间改变。导致这一改变的原因要么是一个人物所采取的一个行动,要么是一个人物对其控制力之外的一个事件所做出的反应。无论何种情况,该事件颠覆了其生活中的一个利害攸关的价值负荷。
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当转折点围绕着揭示或决定旋转的时候,一个事件的硬币两面效应便变得生动而清晰。
就揭示而言:在《唐人街》的第二幕高潮中,主人公J。J。吉提斯(杰克·尼克尔森饰)指控伊芙琳·穆瑞(费·唐娜薇饰)谋杀了她的丈夫。作为反应,她坦白了,但不是承认了谋杀,而是承认跟她父亲乱伦生下了女儿。吉提斯立刻意识到是她的父亲诺亚·克罗斯(约翰·哈斯顿饰)杀了他的女婿,因为他要非法占有他的外孙女女儿。这一对真凶的揭示突然之间便将情节从负极颠覆到了正极。与此同时,我们对伊芙琳便有了洞若观火的了解——她所遭遇的一切,以及她与变态狂父亲做斗争的勇气。
就决定而言:在这个节点上,吉提斯可以打电话报警,把他的证据交给警方,自己退居幕后,让警察来逮捕诺亚·克罗斯。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亲自追捕凶手。这一选择将主人公的情节
转化为危险的负极,同时将聚光灯对准了他的致命缺陷:盲目自傲。吉提斯是那种宁愿冒着生命危险也不轻易求助于人的男人。
事件和人物这两个术语指称的只不过是转折点上的两个角度。由表及里地审视故事,我们会将其视为事件;由内而外的话,我们便将其作为人物来体验。若无事件,人物便无所作为,抑或什么也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若无人物,则无人导致事件或对事件做出反应。
即如亨利·詹姆斯所言:“除了事变的决定性,人物还能是什么?除了人物的说明性,事变还能是什么?一个女人用一只手撑着桌子站着,用某种眼神看着远处的你,这便是一个事变。如果这还不是一个事变的话,我认为就很难说它到底是什么了。从我们所能理解的任何意义而言,人物便是动作,而动作便是情节。”[1]
假设你在写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亨利·詹姆斯式“事变”:你的主人公身处巨大的个人危难之中,知道一个谎言便能救他,但他却一手撑着桌子站着,用某种眼神看着一个女人,意图表达一种暗黑的痛苦真相。他的决定和动作将他的人生从正极旋转到了负极,因为他要承受一切后果。与此同时,他的选择、动作及其后果表达了他的性格真相:英勇真诚的男儿本色。
可以说,这是你的故事中最好的场景,尽管很有力量,在其
下游却会产生一个问题。当你完成故事讲述的时候,你意识到你的最后一幕高潮失之平淡,而由于你的结局失败,你从开始所做的一切创造性工作也会随之而终告失败。怎么办?你可以在以下两个地方找到补救办法:人物或事件。
事件设计:你可以颠覆转折点。你不要让你的主人公讲真话,而是利用谎言来博取权力和金钱。这一改写也许可以为满意的高潮设置伏笔,但它同时也彻底地颠覆了他的道德内核。他现在成了一个腐败的富豪。如果你喜欢这个人物变化,问题就解决了。
人物设计:当你回首去研究你的主人公的心理的时候,你意识到你的高潮缺乏冲击力,因为你的人物过于天真甜美,你的结局很难令人信服。所以,你降低了他的道德亮度,然后将其改写为一个强悍的幸存者。你如何表达这一人物真相的改变?重新设计事件,将其新的狡诈的双重自我戏剧化。如果这些新的转折点能为高潮处的一个强劲分晓埋下伏笔,问题就解决了。
为了明确起见,我们还必须重申:一个情节事件会扭转一个人物生活中的价值负荷;一个人物要么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要么对外部力量所导致的事件做出反应。所以,要改变一个人物的本性,你就必须重新设计事件,以表达他所变成的样子;为了改变事件,你必须重新发明你的人物心
理,使其做出令人信服的新的选择,采取新的行动。因此,无论是情节还是人物的创作,根本不可能存在孰重孰轻的问题。
亚里士多德为何没有看到这一点?一个可能的答案也许在于他对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的赞赏。俄狄浦斯调查一个可怕罪行,结果却发现他自己同时是受害者和作恶者。其控制力之外的事件,他想方设法逃离却逃无可逃的事件,无情地推进着他的命运,并将其碾轧。
《俄狄浦斯王》是亚里士多德时代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最优戏剧,震撼于其悲剧之美,他便恳请其他剧作家向其崇高魅力看齐。所以,索福克勒斯对命运的不可抵御之力的刻画便很可能打动了这个哲学家,使其高估了事件的价值,而低估了人物的价值。
不过,还有第二个可能性更大的原因,这便是审美常规:雅典的剧作家在写作时并不知道潜文本为何物。事实上,演员都戴着面罩来表达其人物的本质。如果一个人物对另一个人物撒谎,观众当然会意识到没有说出的潜文本,但在大多数时候,人物所言都是完全彻底的心声。因此,亚里士多德便更看重所发生的事,而不是事件作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