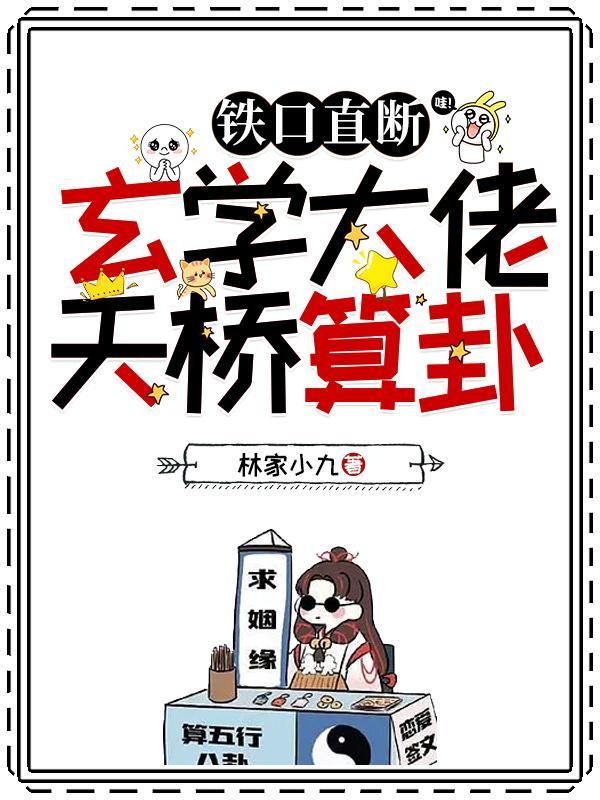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小满亦动人作文800字 > 第81章(第1页)
第81章(第1页)
碧芳没想到她这么快就答应下来,凑到近处正要开口,还云没来由冲她笑笑,顿时眼前一暗,头晕目眩,剎那间没有了知觉。
还云在背后用暗藏的袖箭磨了许久,直到此刻才把绳索割断,她将碧芳击晕,却不敢贸然去杀周词,此处氛围布置、仆从下人皆非比寻常,因怕另藏玄机,她遂纵身从窗口跃下飞快离去。
夜半时分人烟稀少,但本朝并无宵禁,沿街还有不少酒肆店家通宵达旦地做生意。
还云大步走至城南,市中有一家小门面的铺子,里头灯火通明,尚在营业,上方店招写着:洪福蜡烛铺。
还云径直入内,里头摆放着各色蜡烛、烛台和花灯,齐整有序。
店内静谧无声,只有烛火燃烧时不时爆出的轻响,往里,柜台旁斜靠着一个中年男人,半仰着头睡得正香。
还云走至他跟前,两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夜里看去有些骇人。他有所察觉,立时醒来,刚看清眼前是谁,便把眉头拧成了川字。
“你怎么又来了?半个月找我三四回,比索命鬼跑得还勤,我不是早说了吗,我真不知道魏长风所缺是何事物。”
还云随手拿起一支红烛照到他眼前,逼问道:“那你当初怎么知道我才是此事的关键?”
那男人缩了缩脖子,小声道:“我是鬼差,不是阎王,当然只知晓个大概。”
“你明明翻看过生死簿!”红烛举到他跟前,再往前一寸就能烧到他眉毛。
他边躲边站起来,斜跨出两步慢慢走到一张小桌前,嬉皮笑脸地说道:“莫慌莫急,咱们今天就把这事说清楚了,省得你成日担惊受怕。”
他迅速将凳子拉开,邀她坐下,还云还在疑虑,那鬼差已经奉上茶和点心,颇懂些人情世故。
四周灯烛摇晃,花灯乱人眼,他手掌一挥,把各色花灯里的火全灭了,端起杯盏啜了两口:“我壬寅,区区一个鬼差,当初看到几本生死簿已是偶然,还能一个字一个字看完吗?”他叹了口气道,“我知你救主心切,但我也不可能空口编出个故事来,你就别为难我了。”
还云早已一口饮尽了水,转着杯子半信半疑地看他:“当真?不是因为怕被捉回冥府?”
壬寅立马抱拳求饶:“千真万确!就差跪下来给你磕头了。”
还云抬眸看看他,壬寅又继续说道:“你若跑去阎王那儿说出我的所在,我更是难逃一死,把柄在你手中,我岂敢骗你?”
还云一言不发,仍旧直视他,一排排烛火照着他的眼睛,黑白分明。
她默默放下杯子接受了,既问不出所以然,她也不想再耽误时间,起身要走。
壬寅上前虚拦了一下,问道:“我在人间躲了这么久,你怎么找到我的?没有告诉魏长风吧?”
还云扫了他一眼,淡淡说道:“没有。”
“义气啊!”
壬寅笑笑,还想说几句调侃话,还云已背身走向门口,火光投在她背后拉出一道长影,冷峻、孤傲以及一丝难掩的女儿家的纤柔。
她本不该如此。
“等等。”壬寅叫住了她。
彤彤光照下,他正色道:“还云,你的恩早就报完了,情,实在是用错了人。”
“他不一样。”
“他……”壬寅摇了摇头,“我与长风相识数百年,真心将他视作朋友,但你想想,凡间的酒、妖族的酒,如何灌得醉冥界鬼差,引我说出生死簿的内容,以至泄露天机险些魂灭?”
还云显然并不想听这些,壬寅却执意走到她面前,迫使她听下去:“再想想,他以妖魂入了凡人的肉身,才多久,竟能在眼花缭乱的官场坐上朝廷命官的位置,他的心思是你不能及的,别为他那样的人……”
还云打断道:“你不必和我说这些。”
“我是在好言相劝,说到底,若非你向我供奉了所有寿数,我也不可能冲破地界牢笼跑到这儿来躲着。”壬寅耸耸肩,恢复了先前吊儿郎当的样子,掐着手指算起来,“你原本平安顺遂,到古稀之年寿终正寝。”
还云哼笑道:“这副身躯若不受损伤,可以百年千年地活下去。”
壬寅一愣,无奈道:“个中滋味只有你自己知道,没有痛感,也无嗅觉味觉,和行尸走肉有何区别,你做这些还是为了他。”
“我要走了。”
还云冷着脸绕开他,这次壬寅没有阻拦,眼见她从铺子里走入昏暗的街巷。
他坐回桌前,自己给自己又倒了杯茶水,还云早已走远,他看向门外延伸出去的小路,指尖摩挲着杯壁,浅笑道:“他可以诈我,我为何不能瞒他?近在咫尺却不自知t,只是可惜了你啊。”
还云离开蜡烛铺,谨慎地躲到城郊隐蔽处,取出贴身藏好的符咒,咬出指尖一点血珠捻在上头,口中念了七八个字,风一过,人已不见。
阴阳两界之间,永夜无尽,终年不见天日。
她就着浅淡怪异的天光一路往东面走,偶有小妖小鬼过境,她既不理睬,也没有敢招惹她的。
行至一处溪水边,她停下步子,垂眸定定看着自己脚下,眼珠一动不动,竟似入了迷。
半晌,她撩起左边裤管,双唇一抿,用袖箭对准脚踝处用力刺了下去,又在表面刮去点皮肉,干净利落。
刀割在身毫无痛感,她眉目没有一丝波澜,但不知为何,内心深处竟有些许畅然与期待……她用原先沾了黑血的布条照旧包好,走到水边弯腰洗手,抬头遥遥看了眼。
临溪有片房子,她径直走入屋内,分外静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