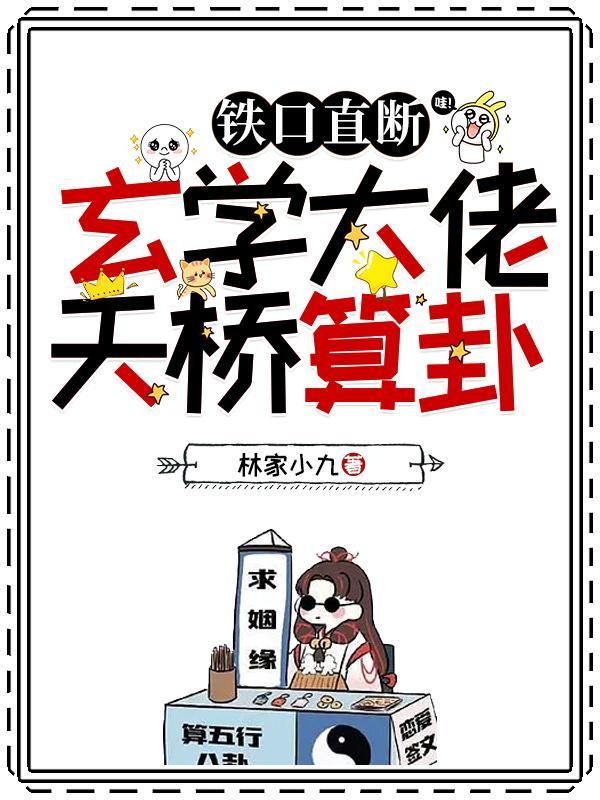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被退婚后我嫁给了年代文大佬 番外 > 第35頁(第1页)
第35頁(第1页)
和到後面根本和不動,還得拖了鞋,光腳上去踩。
下午太陽還沒落山,何叔就把炕盤完了,去水桶邊洗了把手,坐在板凳上開始捲菸。
「抽這個。」陳寄北拿出昨天的喜煙,遞給他一包。
何叔抬手擋住了,「我還是喜歡抽老旱,加個過濾嘴,總覺得沒勁兒。」
倒是夏萬輝有些躍躍欲試,被夏芍一掌拍在後腦上,「你才幾歲,搬桌子吃飯。」
夏萬輝只能捂著腦袋,不情不願去搬炕桌。
盤炕累了大半天,誰都是一身汗一臉灰,得吃點好的。
中午對付了一口,下午夏芍特地去買的菜,張羅出一大桌子下酒。
農家土雞蛋炒了一盤,土豆切絲脆脆點上些白醋。析出的土豆澱粉也沒浪費,和昨天剩下的一起打上個雞蛋,裹在刺老芽上下鍋油煎,煎得外酥里嫩滿齒生香。
刺老芽是一種帶刺灌木的嫩芽,只在春天有,算是山野菜中很好吃的了。夏芍穿越前那會兒因為大量出口,已經賣到了四五十一斤,品相差一點的也要十多。
當時還有人開玩笑,說山上掰刺老芽的人比刺老芽都多。
現在當然沒那麼貴,只是也沒那麼多油炸,夏芍把另外一部分焯水蘸醬吃了。
最後上桌的是一盤花生米,顏色已經炒至深紅,上面灑了一層鹽霜,還在噼啪爆響。
何叔一見拿筷子點點,「這個配酒好,可惜江城這邊不產花生,沒有賣的。」
「是我從關里老家背過來的,這兩年年景不好,有點癟。」
夏芍沒說這原本是準備給李家人的,但李家不做人,她就留下自己吃了。
花生米火候正好,何叔一口氣吃了大半盤,端著小酒喝得美滋滋。夏萬輝倒是一個勁兒在吃刺老芽,總覺得清嫩中帶著微苦,微苦裡又有回甘,比香椿芽還要好吃。
何叔走的時候夏芍給他裝了一些花生,又從抽屜里拿出兩塊錢,「叔您別嫌少。」
「這點小忙要什麼錢?有這個就行。」
何叔只接了花生,拎上工具哼著小曲兒往外走,「我回去了,炕你們燒兩天,烘乾了再睡。」
這年頭盤炕、蓋房子,都是請頓酒,還真少有給錢的。
夏芍沒有堅持,何叔走到門洞,又回頭看看她,對陳寄北說:「你這媳婦兒娶得不錯,結婚了就好好過日子,別整天跟二立那臭小子瞎混,我看他沒個好嘚瑟。」
陳寄北沒多說,送完人回來,夏芍正繫著圍裙在灶台邊刷碗。
見他進來,她輕聲和他商量,「我想買點旱菸給何叔,過兩天把小炕也盤了。」
燈光下她睫毛微微垂著,烏黑又濃密,眉眼十分溫柔。
當然她不語出驚人的時候,總是這麼溫柔的,甚至帶著些軟糯。明知道她不是那樣的性子,當她問你餓不餓,幫你打點人情世故,你還是會不自覺覺得你並不是一個人。
陳寄北望著那道側影沉默半晌,才拿起掃帚開始掃地,「你說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