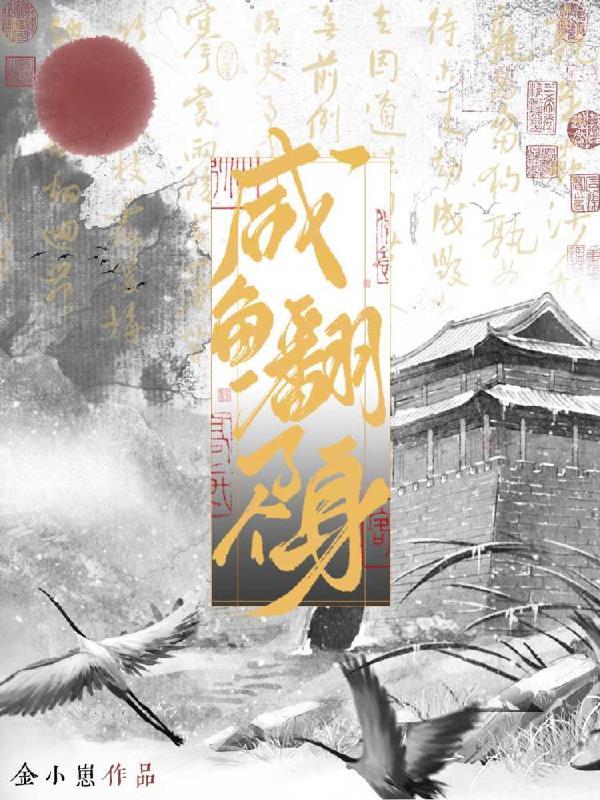笔趣小说>温暖拨动我心弦 > 第13章(第1页)
第13章(第1页)
“你们两个傻子,真有一拼!”我无奈的叹气:魏然周旋在众多的女人中却看着自己爱的女孩是别人的女友;安子低声下气守着魏然看他为别的女孩儿黯然神伤。这两个人过得什么日子呀!
安子依旧失神的盯着我,目光让我觉得很冷。我伸手握住她的手,想给她温暖,却发现她的手滚烫。
“你是不是病了?要不我陪你去医院吧!”我有些害怕。这种状态的她很让我不安,特别是她的眼神。
“不用,我怀孕了,所以体温要高一些。”她冷冰冰的说。
“谁的孩子?魏然的吗?”我快要疯了。
“是。”
“他知道吗?”
“知道,你猜他怎么说。”
我摇摇头。
“他说,‘把孩子拿掉,条件你开,,,,,,’”说着她把脸埋在双手里,泣不成声。
我看见泪水沿着她修长的手指滑落,抽泣的肩无限孱弱。
安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我就是她的亲人。我坐到她身边拥住她,希望给她点力量。她紧紧的攥住我的手,攥得我生疼。
唉,这对儿冤家!心里恨恨的咒骂着魏然这个冷血的家伙,却也不禁有点可怜他。安子口中的他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魏然,却也至情至真,甚至对他有些怜悯。
不对,我怎么可以这么想?他的痴情用错了方式,无情的伤害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拍拍安子的肩,无奈的说:“你爱上了什么样的人呀!”
安子哭得更甚了.
告别了安子,我的心里更是烦乱。
我们往往都是这样:镜中花总是最美的,心中对它无限的企盼,久久不能忘怀,然而它并不一定是最适合自己的。
魏然心中执着的那个女孩子同样不一定是适合他的。和安子这么多年,他们之间不可能没有感情,再过几天比赛就结束了,到时我应该去找魏然谈谈,看能不能挽回,毕竟他们之间还有了孩子.
最近身边的许多人都变了摸样,变得我不熟悉起来:李威、周洲、安子、最让我吃惊的是魏然,仿佛根本是另外一个人。好像只有阿敏还是我原来认识的样子,但是因为章恺的回国,渐渐地也少了联系疏远起来。
其实他们原本就是这样生活的,变化的只是我的心境,我原来竟是这样的不了解他们,这么多年的同学和友人,我对他们的关心其实原本就不够。
自讨苦吃
安子说一会儿还要加班,我已经失去了逛街的心情,和她早早地分了手。
回到校园时还不到中午,想着安子惨淡的情形,原本的好心情被台风吹了一样,无影无踪。我独自坐在排球场边的台阶上,一边发呆,一边等着餐厅的开饭时间。
“周阿姨----周阿姨----”
听见有人喊我,寻声望去,是张老师牵着炎炎的手在校园里溜达,我冲他们笑着招了招手。
一老一小很是亲密,看来相处的不错。
炎炎笑颜如花,一只手不知捏着什么,举得高高的,蹦蹦跳跳地向我跑过来:“阿姨,你看你看,张爷爷给我买的跳跳糖。含在嘴里能爆炸!给你吃!”
垃圾食品!这种糖我吃过。
我接过那块糖,剥开,放进嘴里,小姑娘等着看我的反应。
“真的呀!真的会爆炸呀!”我夸张的说。
炎炎满意的看着我的反应,嘻嘻嘻的笑了。
张老师这时也走过来了,看炎炎的神情就像看着自己的“孙子”,眼睛亮亮的。我打趣他:“老爷子,这么早就领孩子出来玩,今天的课上完了吗?”
“呆在家里憋屈死了,我带炎炎来学校的琴房看看。炎炎,今天看到什么东西了?”
“架子鼓!还有吉他!”炎炎热切的说:“周阿姨,张爷爷说你还会打架子鼓、还会弹吉他、会弹钢琴、会吹双簧管,周阿姨,你怎么什么都会呀!我想看你打架子鼓、还想听你弹吉他。”
她的要求还真多!“好啊,等有时间我给你做专场表演。”对于这个小姑娘我总是不忍心拒绝。
“周阿姨,张爷爷说要带我去游乐场,有过山车!”炎炎兴奋的说。
“哦,是吗?”
“嗯,新建的游乐场这两天刚开放,听说是咱们省规模最大的,比旧的大两倍。五一以前很多设施是免费的呦。”张老师冲我眨眨眼:“小周老师,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呀?”
和安子分手以后心中的种种不快需要宣泄一下,我痛快地答应:“好!”
看孩子远比我想象的要艰难的多!我和张老师领着这位年纪不大却无比活跃的千金小姐着实有些伤神。
炎炎说她从来没到游乐场玩过,开始还有些不信,后来我就相信了:一进游乐场大门她的眼睛就不够用了,“哇!哇!哇!”地赞叹个不停,每种游戏她都要上去玩玩,尖叫着、蹦跳着、哪有点平时小淑女的样子!
酷热的天气,刺眼的阳光,我带着一老一小:又要买票、交钱、又要盯人。小姑娘时不时还要喝可乐、要吃冰淇淋、要去卫生间、要做旋转木马、要看木偶剧演出经常是一转头看到什么,一边喊着一边就冲了过去,我们紧盯着,有时追都追不及。
游乐场里人山人海,全都是和她一般大的孩子,炎炎混在其中根本盯不住,里稍不留神,就会走散。一看不见孩子我就扯着嗓子大声喊:“炎炎----炎炎----”把她走失了可就完了!到后来张老爷子也有些跟不动了,好不容易排到一张空着的椅子,赖着坐在上面就不走了。
唉!借别人的孩子出来玩,真是找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