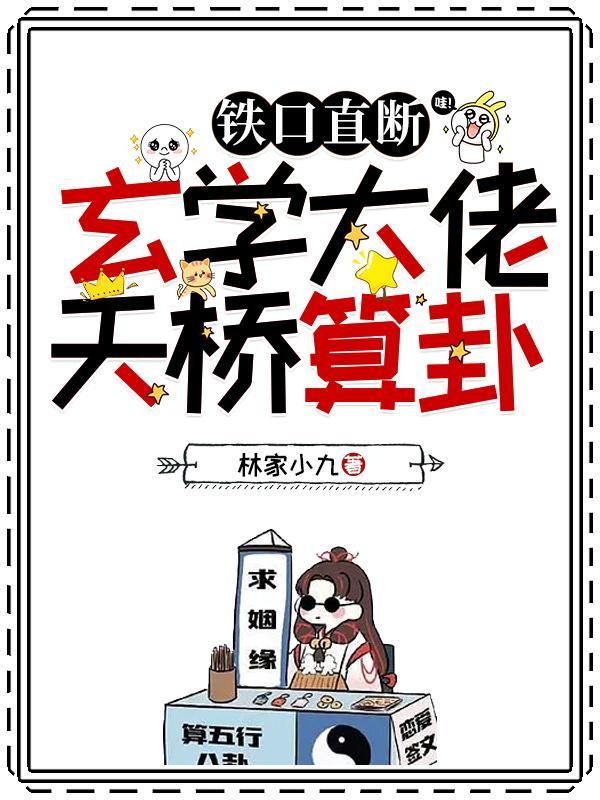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感觉鬼压床动弹不了 > 第55章(第1页)
第55章(第1页)
季鹤存了心思,站队时让乔横林站在自己前面,果然两个人分到了同一个连队同一个寝室。
至少这样,乔横林不用每天都跑到他面前翻仅有一个的行李箱找内裤穿。
寝室很大,能住二十个人,钢架单薄的上下铺,扑面而来的霉味儿让季鹤几近呕吐。
乔横林抢了靠窗头一个铺子,这里除了跟后面的上下铺挨着,不像中间的大通铺,前后左右都有人。
行李塞床底下,季鹤本来要住上铺,但上铺床单有污渍,乔横林就把干净的下铺让给他。
初到新鲜环境,大家不免自觉抱团,试探着跟周边人攀谈。
季鹤是没什么心思的,但大家对他最好奇不过,没办法,谁叫他的长头发太显眼了。
但他的出色五官上凝结的冷意更明显,没人敢主动开口,便向跟他一起同行的乔横林示好。
乔横林有问有答,笑起来相对面善,说话时会先介绍季鹤再介绍自己,仿佛是他的代言人。
热闹了一阵,门外响起口哨,教官让他们出来排队,带到大太阳底下领队服训话讲规矩。
季鹤连教官的脸都没记住,只听到一个班三天才能去一次澡堂,一次五分钟。
乔横林心态还好,哪儿都能睡怎么着都行。
就是吃饭不香,这里的米饭夹生,比季鹤蒸得差远了,汤一点儿料都没有,季鹤煮的粥喝完涮锅都比它好喝,菜炒得又老又油,还没有肉,季鹤烫个青菜都胜过百倍……
乔横林在心里默默比较,看到季鹤也没什么胃口,就大口扒饭,跟在他身后离开饭桌。
季鹤回宿舍一屁股坐到床上,他以前从来不穿外裤上床,现在谁还分得清是裤子脏还是床脏,只觉得全是细菌,全是虱子,浑身就像有虫子在爬!
杀鸡
季鹤睡不着,乔横林也不乐意睡,时不时往下铺探头,捏着嗓子用气音顶出去问季鹤感觉还好不好。
不好,当然不好。
季鹤心情很差,他的眼梢原本是微微上翘的,虽然看起来容易显得散漫淡然,但一向很有精神,现在却显得有气无力,他既不想闭眼,也不想看见上铺木板上发霉的菌斑。
“季鹤,要不要枕我的衣服睡觉?干净的。”
乔横林双手把住腰,利索地扒下贴身短袖,从上铺斜出身子。
季鹤避开眼前更深的阴影,侧头从窗户里捕捉从帘子缺口倾泻的一块儿莹白的光斑,轻声回应,“不要,你穿上吧,要是光着身子睡这样的床上,以后就离我远点儿,好脏。”
乔横林从来不觉得季鹤是开玩笑,他委屈地缩回手,又不分反正地把衣服套了回去,扯了扯过紧的领口,又顺势躺下。
这铁架加木板的床大概比他们年纪还大,垂暮老人般不经折腾,他这一动一动的,嘎吱嘎吱的噪音格外难听。
睡他们旁边上铺的男生早就被寝室连番的呼噜声吵得睡不着,被乔横林的动作一激,直起身子抬脚踹了他们相连的床头铁架。
“能不能睡觉?”
季鹤先是感觉床铺猛地震动,随即听到那男生憋着火喊了句,乔横林似乎也要坐起来说什么,季鹤赶紧说。
“乔横林,快睡吧。”
乔横林半起的身子滞了滞,又缓慢地躺了下去,除了呼吸声重了些,也没什么别的表现。
季鹤以为自己的安抚有效,实际上他所看不到、乔横林也永远不会对他施展的眼神,凶狠到陌生,那人再踹一脚,他就能跳过去撕咬干仗。
但季鹤的话他要听,让他停就停,让他睡就睡。
经过这段插曲,季鹤愈发睡不着,半夜听到不知道哪里传来的啜泣声,他心脏为此提了一下,扬起身子靠近上铺的木板。
他本来以为一定是性格软弱的乔横林因为刚才被人说了一嘴而伤心着,季鹤这样的主观评判也没错,因为乔横林平时也是,虽然小错不断,但某种方面,听话到逆来顺受。
所以他想当然地认为,乔横林是需要被保护的、很容易委屈的、一刻也离不了人的。
被他这样念着的乔横林,心大到早就发出轻轻的打鼾声,季鹤听见时也感觉很无语,嘴角忍不住撇了两下。
他没有再刻意探索哭声出自哪里时,那人却不打自找,正是在他们上下铺旁边,刚才找事的男孩儿的下铺,正缩在被子里发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季鹤记得他的名字,刚到寝室乔横林跟别人打得热火朝天时问过他的名字,他嗓子黏黏糊糊地给出三个字,尤小勇,小勇,是勇敢的意思还是勇气的意思,不管哪个,都跟他现在胆小哭泣的模样大相径庭。
季鹤不是多事的人,根本没有要安慰的意思,转了个身子强行闭眼,好让刚才紧张的心脏舒服一些。
很快外面响起烦人的哨声,有巡查的教练在外面扯着嗓子叫门,喊大家起床。
乔横林哼唧两声就爬了起来,视线跟昨天踹床架子的人对上。
闹了矛盾,眼神自然应当微妙起来,可那人却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维持一贯的吊儿郎当,没踩爬架,从上铺直接跳了下去,稳稳落地。
乔横林虽然因为他害得季鹤说他而恼火,但他是不怎么记仇的小狗,看人家没表示特别的恶意,也将昨天的事抛诸脑后,笑嘻嘻地问季鹤自己叠的被子好不好。
“不好,检查不会过关。”
季鹤客观评价乔横林叠得很粗糙的小方块儿,不像是军训过的豆腐,像摔在地上软趴趴的毛豆腐。
昨天教官示范过折叠方法,乔横林的小脑仁根本装不下,这下正犯愁,但犯愁的不止他一个,教官还在外面不停催促,瞧着马上就要进来检查,不会叠的人全心慌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