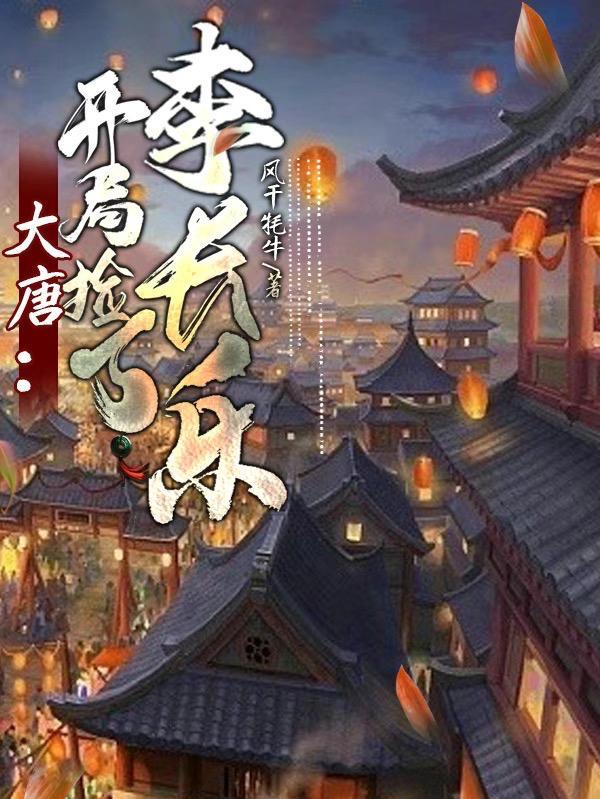笔趣小说>残花是什么 > 3我们竟又相距这么近(第1页)
3我们竟又相距这么近(第1页)
周日,我六点半起床出去锻炼。做了准备活动后,沿着人行道跑了半个小时,又快走了半个小时。我长期失眠,但不敢吃安眠药。妈妈当年换了多种安眠药,每次用一阵子就失效。跟她在一起时,我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她连续几天睡不着。那样的日子我不想重复。怕对安眠药产生耐药性,我只能寄希望于锻炼。到美国后我每天跑步。失眠问题没有多少好转,甚至在妈妈去世后进一步恶化。但我相信,如果不是坚持跑步,我恐怕早已经疯了或死了。
在清晨阳光和新鲜空气的沐浴下,跑出一身汗,心情会轻松舒畅一些。这是我一天中感觉最好的时刻。
我洗完澡回到房间,顺手带上门。刚把内衣穿上,门突然被推开,蒂尼思的儿子杰弗瑞站在门口。我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他已经窜了过来。他只有十五岁,但比我高出一大截。这么个又高又壮的黑人小伙子突然紧贴在我身边,我吓昏了,冲口用中文喊道:“你要干什么?”
他没有看我,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的书桌,用右手捂着右耳朵,头往右边歪,不停地蹦着、笑着、嘟囔着。过了几秒钟,我才回过神儿来。他并没有要侵犯我的意思。我改用英语问:“你到我房间来做什么?”他没说话,也不理睬我,继续歪着头蹦着、笑着、嘟囔着。他的笑很怪异。另一种恐惧袭上我的心头。
杰弗瑞的外婆来到门口,说了声对不起,走进来把杰弗瑞拉了出去。
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回事。两年前我第一次来看房时,杰弗瑞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他在妈妈身边捂着耳朵不停地蹦。我跟他问好,他不理我,接着蹦。我笑着对蒂尼思说这孩子看起来很害羞,她没说什么。这两年间,我早出晚归,很少跟他碰面,也没跟他讲过话。仔细想想,他好像的确不大对劲。看那样子,可能是有什么病吧。我想不出个所以然。没人跟我讲过蒂尼思有什么病或这孩子有什么问题,我也不想多嘴多舌地乱打听。
我吃完早饭便去了学校。自从来到B大,我几乎天天都泡在学校里,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我必须尽快恢复以前的生活规律。我住得离学校不远,走路三十分钟就到。一路上我脑子里全是蒂尼思家的几个人。夫妻离异,身染重病,孩子又有怪病……是不是天底下所有的人都有这么多痛苦?是不是人生注定要饱受煎熬?
到了办公室门口,我拿出钥匙,插进锁孔,盯着门锁上方的那小幅黑白漫画了一会儿呆。一群牛在狂奔,下面题了一行小字:asifeverybodyknosheretogo。简直就像专为我画的一样。我在狂奔,却不知道目标是什么,更不知道归宿在哪里。画纸明显泛黄,想必贴在这里很多年了,二十年?五十年?当初贴它的人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迷茫?他或她现在已经步入中晚年了吧,有没有弄清目标和归宿?这么多年来,这里进进出出若干学生,是不是也有人跟我一样会时不时盯着它呆?
我们办公室五个人中只有费尔德和我是同期入学的,另外三个人入学都比我们早。他们来无踪去无影,只是偶尔来拿点东西或待上一小会儿。我经常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见上他们一面。搞不清楚他们平时都待在哪里。我们系博士生毕业的平均时间是六年半。熬上七、八年才拿到学位的大有人在。这些人有他们不为我所知的世界。也许他们平时待在家里?或者边工作边写论文?费尔德喜欢泡在图书馆或机房。多数时间,办公室里只有我一个人。
出乎意料,今天费尔德在。看我进来,他把翘在桌上的两条腿拿下来,转过身来跟我打招呼。他满脸倦容,眼睛里充满血丝。我问他是不是又没回家睡觉。他苦笑着说,帮教授做的东西快到截止日期了,没办法,只好连夜干。我把背包放下,去了机房。时间还早,机房里只有一个人。我选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我喜欢这个位置,可以时不时看看窗外的蓝天白云绿树呆。
希望今天能静下心来做点有用的事。
开机后,我习惯性地打开邮箱,一眼看到已经四年没有见到但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名字–周密。我的心紧跳了一下,打开他的邮件,只有一行字:
“你还好吗?我已经读完mBa,现在k城工作。”
k城,来B大开车只要一个多小时。他竟然跑到这边来了?!
离婚后,我切断了与他的所有联系。他曾委婉地提出想要保持朋友关系。据说有人可以把前夫当成朋友,但我做不到。保持联系会让我不断地想起离婚前的混乱,我恼他、怨他、恨他。这种痛苦很没意义,不是吗?烦心事本来就不少,还要被过去的事过去的人折磨,岂不荒唐?我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时总是提醒自己:周密已经是过去时,我未来的生活里再也不会有他,那些跟他有关的痛苦已经过去了,不应该影响我现在的生活,更不会影响我今后的生活。恨一个人是跟自己过不去,让自己难受,你恨的那个人却一点不受影响。所以,不要恨、不要想,要忘记他,要忘记跟他有关的一切。也许时间是一剂良药,也许强制性遗忘起了作用,也许不恨是因为不在意,离婚的痛苦逐渐淡去,我现在似乎真的不再想他、也不再恨他了。
他怎么会知道我的电邮地址?转念一想,在这个信息社会里,想找一个人总是不难,何况系里的网站上列出了所有博士生的名字、入学年份、办公室电话和电邮地址。我在美国的正式名字是yingLin,没有起过英文名。
当年我大老远跑到美国来就是为了躲开他,永远不再见他,把他从我的生活里彻底清除出去,把他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掉。而今,我们竟又相距这么近?他以前没有出国打算的,怎么也来了?还读了mBa?在哪个学校读的?现在做什么?在哪个公司?为什么要来k城?总不会跟我有关系吧?我呆呆地胡思乱想了好一阵子,最后想到,不管他怎样、在哪里,都跟我无关,我不想再跟他扯上一丝瓜葛。
我把他的信删除,关掉邮箱。
我开始硬着头皮给讨债公司写信。那天给拖车行打完电话后,我没再碰那份账单。我把它压到抽屉的最底层,尽量不去开那个抽屉。我知道我不该逃避这个难题,但却实在没有力气去应对它。拖车行最后把账单转给了讨债公司。我不能再拖着不管了。我打算给讨债公司写信,讲述我的困境,请求他们把债款降低到我有能力支付的数额。写了几行后,一个念头猛然蹦了出来:妈妈去世的消息应该告诉周密。
她曾跟我们同住过几个月。晚上她会洗好水果端给他,也会悉心做一些他喜欢吃的饭菜。他对妈妈也算不错,温和有礼,笑脸相对,陪她玩牌,陪她去郊游。其实我知道,他们俩都不喜欢对方。在妈妈眼里,比起她那些优秀的学生,他实在配不上她的宝贝女儿。她没有明说过,但从她的眼神和态度中我能察觉到她的失望。我一向心思敏感,尤其对她。自我上大学起,除了不断地提醒我与男孩子交往时不要“过杠”外,她从不对我指指点点,更不会对我的决定提出任何反对意见,最多在我的要求下委婉地给出一些建议。尽管我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最在意的人,但她完完全全把我当作一个成年人去尊重。即便我嫁给一个她不满意的人,她也没有说过什么。对此我感激不尽,也更加敬爱她。周密从开始时就觉察到妈妈不喜欢他,他对妈妈溺爱女儿的做法颇有微词,他认为我的许多毛病,诸如不求上进、不会做家务、乱扔东西、胡搅蛮缠不讲理,都是妈妈给惯的。尽管如此,在我们三人共同相处期间,他俩都把对彼此的不满掩藏起来,维持了一段表面和睦的家庭关系。
大家毕竟在一起生活过那么长时间,而且都尽力做过让对方开心的事。我点开垃圾箱,给他回复了一行字:
“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一个月前我妈病逝了。”
我觉得这么做就是例行公事,没有动机,也不期待结果。我只是把该做的做了,仅此而已。
我继续给讨债公司写信。把困境讲完后,开始斟酌该用什么样的措辞来恳求他们降低债款额。这样的事以前没干过,既不知道该怎么说,又觉得有损自尊,而且用英语写东西总是像隔靴挠痒,没法恰如其分地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正在苦思冥想时,费尔德在机房门口喊:“林樱,你的电话,打到办公室的。”
刚开学时,同学们按照习惯不叫姓只叫我的名—ying。我觉得别扭。我不喜欢跟人走得太近,单字的称呼显得暧昧。当然我明白这只是我的怪想法,美国人中单音的名字很常见,Joe,kay,Jay,guy……可我觉得只有最亲密的人之间才会叫单字。我不厌其烦地要求老师和同学们叫我“Linying”,或者叫我“Lin”。不知他们是否觉得我莫名其妙,但嘻嘻哈哈间大家还是顺从了我的愿望。
谁会给我打电话呢?我没有给过任何人办公室电话号码。只有系办的人偶尔打电话来找我,可现在是周末,她们不上班。两年前上微经课时同学们经常打电话来讨论作业。自从过了鬼门关后,大家各忙各的,再没人打电话了,有事都是写邮件或直接来敲门。会是谁呢?我关掉电脑上的文件,退出账户,走出机房。费尔德神秘兮兮地压低嗓音说:“是个男的。”
回到办公室,拿起电话,竟然是周密。我一下子愣住。直到他再次叫我的名字,我才回过神来。费尔德拿起书包,对我摆摆手,眨眨眼睛,意味深长地笑笑,离开了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