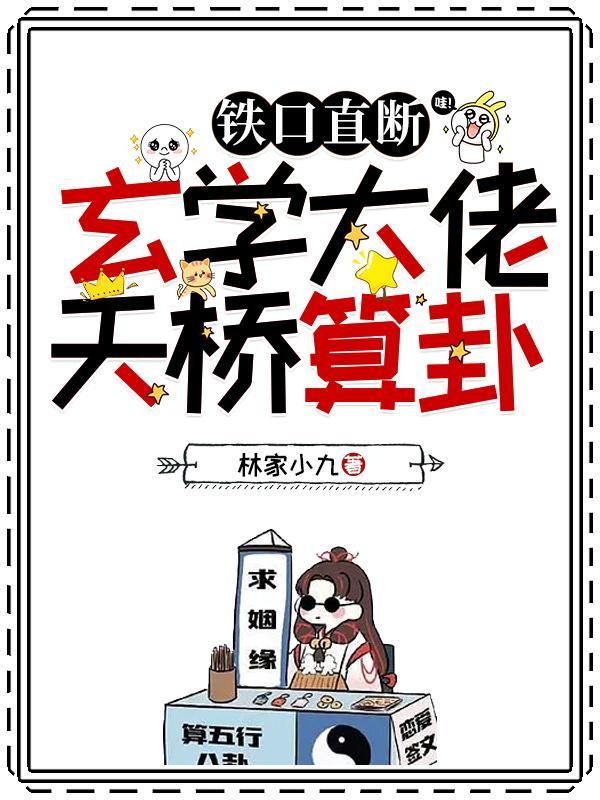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睡觉感觉有人抱着我动弹不了 > 第2章(第1页)
第2章(第1页)
季鹤勾了下脚背,想要从凳子上跳下去,季君知道他是不耐烦了,便伸手在空气里象征安抚地按两下。
这回嘴皮子利索了,“就那小孩儿,跟狗抢馒头吃,黄秋风说可能是城东路孤儿院里的,前两月倒闭之后,跑丢不少小孩儿。”
“你,”季鹤拧两只弯眉,“养不了他。”
季君多大人了,季鹤才多大,可就是身份颠倒地被抓了心思。
季君吾哩哇啦地嘟囔一句,“瞧他像小狗,馒头就能活。”
“这个月电费涨了,你不要半夜偷偷开风扇,蒲扇也是能用的,”季鹤从凳子上一跃而下,捋平胸前的衣襟,“他不许进屋,跟你睡,明天丢掉。”
说罢他便绕过书柜背板,出了卧室,又顿住脚步。
天昏黑了,门厅前的小孩儿还在那儿站着,因为肤色深,倒很不显眼,他手里攥了东西,是季鹤刚才落在地板上的抹布。
地上泥汤和脚印已经被擦干净。
季鹤忍不住打量。
他的裤子很不合身,肥得堆积在脚踝上,站着也像蹲着,油黑的头发乱糟糟,因为淋了雨,贴了几撮在眉间,差点儿就挡住那双看起来就笨的大眼。
季鹤明白为什么季君说他像狗,的确很像。
“过来。”季鹤突然开口道。
小黑孩儿身子向前微倾,脚却钉钉子似的没动。
季鹤立即感到失望,他不是招手即来的小狗,只是风雨里安如山的榆木。
他索性不管,回到柜台后的藤椅上,将刚才撩下的书重新翻开,手腕微微用力托举,十根手指各自安放在书封书脊上,细慢地默读。
期间余光掠过门口,季君把人领进屋,抓他的胳膊才肯走,所行之处留下两排蹩脚又肮脏的脚印。
季鹤将眼神埋回书里,略过一行字又再回头重看,竟没读出个意思。
他又放下书,抽屉里拿了条新抹布,伏在地上将脚印擦光。
指针刚过八点,季鹤准时换上干净的米色拖鞋,裹着薄薄一层浴巾站在浴室门口,正撞见季君出来,怀里抱着赤条条的小男孩儿。
“你先别进去。”季君慌乱用脚抵住玻璃门。
季鹤轻轻歪头,盯着季君怀里的人看,洗干净之后,他好像比原先白些,至少肤色是均匀的,发根硬挺,每根头发都是先冲天再折下来,脑袋像春风吹又生的草圃。
季君发觉季鹤淡色的唇好似翘了翘,就趁机溜走了。
等季鹤回过神,推开玻璃门,顿时喉头一紧。
浴室原本就是硬挤出来的平方米,窄小的甬道纳不住太重的热气,铺天盖地地冲向季鹤的门面。
水槽堵死,灰黑色的脏水一直蔓延到季鹤的脚趾,花撒丧气地垂在地上,沾了几条粗泥条。
这股水味儿令季鹤感到恶心,他啪的一声甩上浴室门,手心抵住痉挛的胃,缓了好大一阵儿才挪回卧室。
见他进来,季君先天不足的心脏一紧,毛巾在那捡来的小孩儿头上一呼噜就赔笑脸道:“这是我的毛巾。浴室……我明天就收拾出来。正好你来了,借他件儿衣服呗,我的太大了。”季鹤不语。
季君又说,“那明天也不能让他顶着我的老头衫送去孤儿院吧,搞不好怀疑咱们虐待呢?”
他手底下的小孩儿一激灵,瑟缩的肋骨剧烈起伏,但又有意屏息不敢发出声音,似乎是从季君的口气里察觉到谁是这家里的主人,于是害怕地盯着季鹤,露了几颗牙齿,很紧张的笑意。
季鹤转过身,拉开柜子,拿了件白色短袖和他从来不穿的短裤,尽管是扔过去的动作,但并不算粗暴。
可恰逢季君脚麻,朝后挪了半步,那衣服正正落在小孩儿的头上,季鹤轻轻皱了下眉头,眼皮落下去。
“晚上我要洗澡,浴室现在就要收拾,你把地拖干净,花撒洗手池我来消毒。他不能跟我睡在一起,跟你睡躺椅。”
“好嘞。”季君拽走小孩儿头上的衣物,拉着他离开卧室。
他这才重获光明,一时模糊了方向,摇着脑袋,不留神瞥见即将关合的门内,浴巾褪到腰窝的季鹤。
季君把他抱到藤椅上,拿出短袖套头,他便自己伸出胳膊去扯。
“你会穿衣服,真厉害,”季君递过去短裤,“这条是黑色的,季鹤不喜欢,没穿过。其实还挺好看,你穿着刚好,但是是不是有点儿松……改天给你换条。今晚就这么睡吧,成不?”
小孩儿亮着眼睛,慌乱地点点头。
“这个年纪该会说话了呀……难不成是个哑巴。”季君小声嘟囔着,着手去收拾浴室。
横林
刚撸起袖子,身后闪出来个小影儿,小孩儿光脚跑了出来,比他先一步弯下腰,两只手合拢,将地上的水往水槽里舀。
“你要帮忙啊,”季君一笑,“那你帮我举着花洒头就成,不过你待会儿光脚出去可不成,踩一地水,季鹤要发火咯。”
小孩儿跟随季君笑,又露出牙齿。
被他们念叨的季鹤正在门口,挺了挺脖颈,转身回到卧室,将怀里的凉席推回墙角,坐回板凳上,捻了一支新毛笔,沾墨写着。
季君捯饬得很快,他知道季鹤根本信不过自己,不管怎么样都是要自己再打扫几遍的,便余出时间给他。
叩门叫过季鹤后,季君重新把小孩儿抱回去,藤椅下横躺一个夏凉席,差点儿把他绊倒。
他铺开,躺下去才问,“你要睡哪个呀,凉席好…凉席宽敞……”
说罢,便响起了鼾声,季君兀自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