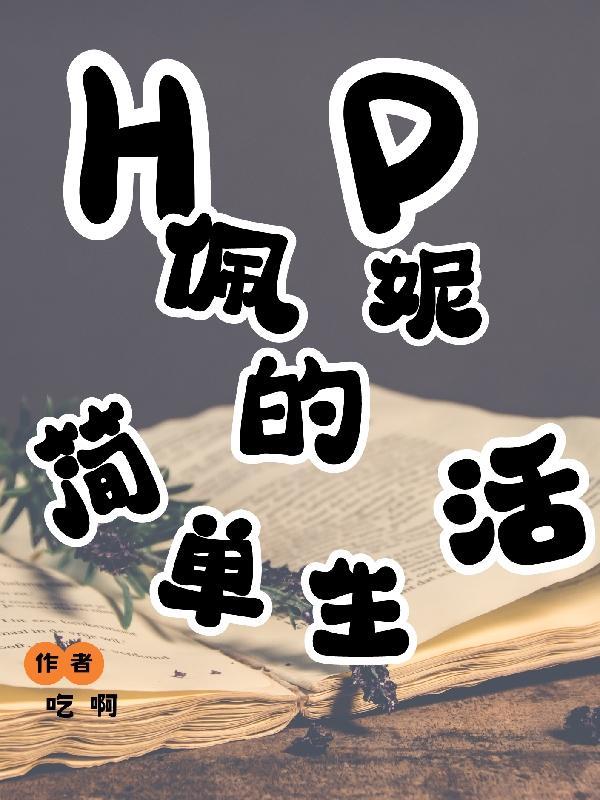笔趣小说>金戈力哥 > 第五回美人彀中第六章(第1页)
第五回美人彀中第六章(第1页)
刘兴隆听了吉义问话,呵呵笑道:“倘若我们野法师关牢里还能用法术,官家得有多傻?”
张晋道:“刘兄莫卖关子。吉兄,我来说与你知。只因我们吃的牢饭,与别的犯人不同,饭里掺有一种叫做艾根散的丹药,能使人法力散竭,并且持续一段日子,令人法力聚不起来。”
吉义点头道:“原来如此。”
钱季宝补充道:“不单法师,武师其实也一样。吃了艾根散,法师没法力,犹如废人一般;武师没内力,犹如常人一般。只因法力和内力都是灵力,叫法不同而已。”
吉义又点头道:“这个我知。”
刘兴隆道:“吉兄,方才我并非有心卖关子,只是奇怪,吉兄既是妖人,为何连囚犯无法施法的缘故都不知道?敢情吉兄你自己吃了牢饭还能用妖法?”
吉义叹道:“刘兄,我哪里是甚么妖人?会用甚么妖法?我一介良民而已,委实是半个妖法也不会啊!如今却被诬为妖人,岂不冤哉枉也?”
众人又是一阵哈哈大笑。他们在牢里聊天,苦中作乐。另一边,知府与夫人在饭桌上饮酒叙话。
蔡夫人闲闲问起:“对了,那个小算命的,官人还没把他处死么?”
慕容知府惊道:“夫人怎么知道?”
蔡夫人一笑:“官人被人说成要戴绿帽,也不告诉奴家?奴家听到传言方知,心想他说的倒也不错!”
慕容知府慌道:“这、这……这话怎讲?”
蔡夫人伸出一根手指,往知府额上一点:“这种事官人都不与我说!将来必敢瞒着我在外头纳几个小妾,管得不好真个会为你戴上绿帽子,也未可知!”
慕容知府大慌:“下官不敢!”
蔡夫人哼道:“有什么敢不敢的?我倒问你,那小算命的何时处决?”
慕容知府道:“我已判他死罪,死囚秋后问斩,乃是惯例。”
蔡夫人轻轻摇头:“官人,算命的皆爱耸人听闻,借此坑人钱财。你为何偏要找他算卦,自取其辱?你可是新任知府,应当注重名声。他敢辱你,你应当尽快除之,免得传言流播,惹人耻笑。更有甚者,万一传到上官耳里,嫌你不能修身齐家,岂不有碍仕途?”
慕容知府听了头冒冷汗,忙道:“贤妻教诲得是!下官这便令人除害,不使那小半仙活到秋天!”
蔡夫人嘴角一撇:“那么活到何时?”
慕容知府用力一握拳:“只活到明日为止了!”
蔡夫人这才露出满意的笑容,与知府交杯畅饮。
侍立在夫人身后的心腹丫鬟潘鹂儿,听了他们的言语,再度不寒而栗。连个小算命,稍有泄露夫人行径之嫌,夫人都急于将其杀死。那么,自己知道夫人许多不可告人之事,岂不是更该死了?纵然她现下还放心自己,倘若哪天不放心了,要除去自己还不容易?那时又有谁能救自己?自己自小在相府里长大,对外面的世界全然不知,纵然想逃,又能逃到哪去?
惊恐之下,潘鹂儿反复寻思,觉得惟有铤而走险,想法子去救小妖人……不,小壮士!或者他能够带自己远走高飞!他好歹也算是自己的……男人。看他行径,有仁有义,必不是坏人。当日是他救了夫人和自己,夫人本来许下把自己给他的。如今夫人毁约,不把自己给小壮士,却有意要给知府,收知府的心。自己已经失身给了小壮士,如果再嫁他人,岂不是不贞?
潘鹂儿自小生长在相府,陪小姐读书,深受经书上三从四德、从一而终的教诲,根深蒂固,自然而然这么想。
席散,潘鹂儿再苦苦寻思一番,终于下定决心,拼死冒险一场,要救吉义,跟他远走高飞。
前些天蔡夫人用来擒拿吉义的麻药酒,便是吩咐潘鹂儿照着秘方调配。潘鹂儿还记得那秘方,赶紧弄来原料,再配一壶。拿只狗儿试了试,半杯即倒。
当夜,夜深人静之时,潘鹂儿窥个空儿,提着酒壶,走出内宅。出外宅大门时,就说自己奉了夫人之命要去办事。
看门的几个老仆人有些疑惑,却不敢吭声。在这府里,夫人的人高过知府的人,谁不知潘鹂儿是夫人的心腹,怎敢拦她?老仆人老来经事,自不肯造次多事,得罪夫人。
夜半三更,往大牢的一路上黑咕隆咚,人声尽寂,只有夜猫子不时寒森森地叫唤几声。
潘鹂儿左手打着灯笼,右手提着酒壶,脚步匆匆,心跳怦怦。这一路不好走,她小心看路,只怕打翻了酒壶。
不料,路边一棵大树后面,猛然蹿出一个人影!
那人动作敏捷,一下子蹿到潘鹂儿身后,一手掩了她的嘴,一手夺了她的灯笼,将她的身子紧紧揽住,拖到树下。
潘鹂儿被倒拖着走,犹自死死攥着酒壶。四周静寂,没有任何人可救命,为了活命,潘鹂儿使劲挣扎,却被那人一拳打在小腹上,禁不住一下子软倒了。酒壶终于脱手,跌在一边,麻药酒咕嘟咕嘟洒出来。
那人可不管酒壶,将灯笼放好,用一根布条将潘鹂儿绑了嘴巴,然后将瘫软无力的潘鹂儿剥了外衣,穿在自己身上,再脱了她的绣鞋,穿到自己脚上。
原来那人也是个小女子,身材比潘鹂儿略高一些而已。
那小女子穿了潘鹂儿的衣裳、鞋子,提起知府家的灯笼,来回走了几步。见自己活像个丫鬟样子,小女子很是满意,回到潘鹂儿身前,嘿嘿笑道:“造化!你这丫头儿,怎么半夜出来游荡?必是要干坏事儿,活该你遭我的手!我正愁如何去救死牢里的吉哥哥,这下有法子啦。你这衣裳和灯笼,正好借我用用。你虽然无辜,却也留不得!啧啧,你如此秀气,可惜了!”
说罢,小女子从腰间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匕,就要来杀潘鹂儿。
潘鹂儿登时眼泪直滚下来。嘴巴被绑着没法出声,唯有泪如泉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