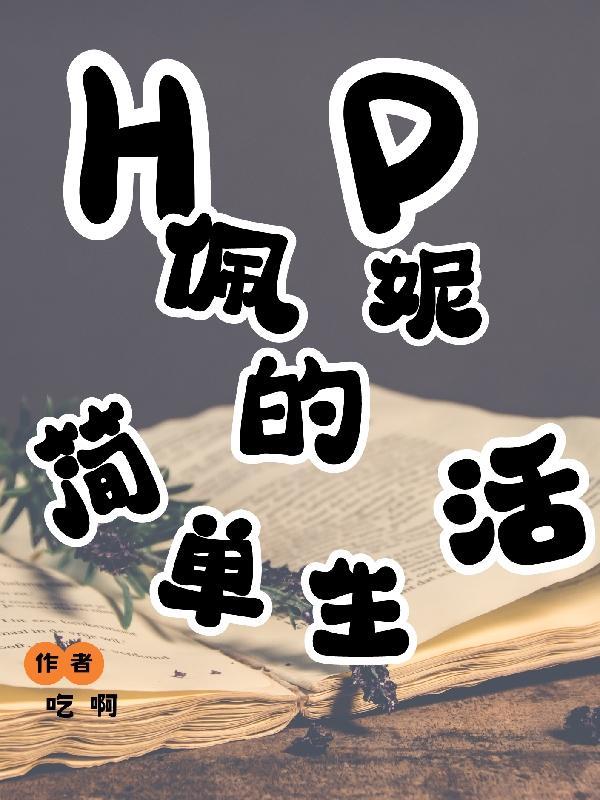笔趣小说>一只狐狸的故事 > 第38章(第3页)
第38章(第3页)
沈万霄捧起他的脸,拇指轻柔地拭去他脸上的泪珠,乌黑的眸子里映出他眉心那朵几欲滴血的红莲。
那是世上最恶毒的诅咒,是他一意孤行在松晏身上种下的咒。
九转红莲,得此咒者生生死死万世轮回,享人间八苦,受七情六欲之痛,千秋万代,死亦无止。
“崽崽,”沈万霄同他额头相抵,捏诀藏去他眉心的红莲,声音沙哑,“你永远不要记起。”
“永远不要。”
“求你了。”
松晏蓦地惊醒,宿醉带来的头痛让他忍不住皱眉。
他披衣下床,隐约间觉得昨晚生了什么,但琢磨良久也只记得单舟横帮他赶走了一个前来找事的人,再往后,便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他来不及细想,便有人敲响房门,于是匆匆整理好衣裳,拉开门只见单舟横咬着一个鲜肉包子懒洋洋地倚在门口,手里还揣着几只绿油油的粽子。
瞧见他时,单舟横的表情显然呆了一瞬,迟疑道:“你。。。。。。头?”
松晏身子微僵,扭头往肩上一瞧,这才觉头已变回大雪一样的白。
好在单舟横自幼拜入婆娑门,见过的妖魔鬼怪不说一万也有一千,此时便也见怪不怪,只说:“你赶紧想法子遮一遮,这要叫别人瞧见了,指不定又要说你是妖女所生,也是个妖怪。”
松晏眼皮一抬:“我本来就是妖怪。”
单舟横:?
松晏慢吞吞地将头拢到身后,回屋找了件斗篷披上,拉起兜帽:“我娘是狐妖,我也是狐妖。”
单舟横咽下包子。
松晏转过身来朝他龇牙:“会吃人的那种。”
“哦。”单舟横面无表情。
松晏郁闷:“你不害怕吗?”
单舟横耸肩:“你要是会吃人,干吗不用法术把头变黑?还这么费力地找斗篷遮头。”
松晏颇为无趣地扫他一眼,抬脚走出屋子。
单舟横剥开粽子,咬下一口紧追上去,声音含糊:“你知道应老婆子什么时候走么?”
“昨日我听她说是今日便回去,”松晏脚步一顿,狐疑地打量单舟横,“你问这个。。。。。。不会是想跟着去吧?”
单舟横一笑:“若要跟着,我便不问了,直接跟去就行。”
松晏想了想,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便没再多问。
倒是单舟横先解释起来:“琉璃灯在应绥那儿,虽然他没明说要琉璃灯做什么,但我大致也能猜到。”
松晏走得有些急,他昨日与步重说好今日要启程去无花谷,但因着醉酒多睡了一会儿,此刻便是要赶着去给李凌寒道别的。他一面听单舟横说,一面脚步不停,闻言也只是微微偏过脸看向他:“琉璃灯只是一个空罩子,灯芯不知所踪,应绥要这灯罩做什么?”
“应绥娘亲走得早,但生死簿上没有她的名字,她便只能日日夜夜地徘徊在忘川河边。应绥不想看她成为孤魂野鬼,便想法子要将她带回人间,但。。。。。。”
松晏忽然停下脚步。
单舟横叹着气道:“她的肉身已经腐烂,若要重新回来,就需要琉璃灯的照拂,不然一具魂魄,难免会被鬼差当作厉鬼捕杀。”
松晏无甚动静,失神地握住胸前那只不知不觉间失而复得的长命锁。
单舟横絮絮叨叨接着道:“虽然说琉璃灯能让人起死回生,但也不是这么个回法。他那日抢走金翅鸟羽,便是想借羽毛上的神力催动琉璃灯,但我没让他如愿,如今便是怕他听信了那些妖道的鬼话,杀人点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