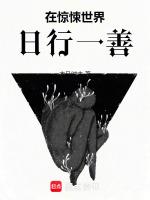笔趣小说>天下长安电视剧在线观看完整版 > 第九十二章有人要屠村(第2页)
第九十二章有人要屠村(第2页)
吴阿奶很急,很怕,她问:“你说什么?”
那人眼神里泛起凶光:“装傻?”
他单臂按着吴阿奶靠在墙上,手开始逐渐力:“村口那个泥塑是谁?叶无坷在村子里还有什么亲人?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
老人家更急了,更怕了,她使劲儿摇头,脖子被掐着她连呼吸都困难,也就更说不出话了。
“妈的。”
那人骂了一声:“跟我装聋作哑?那就从你开始,反正这村子里的人一个都活不了。”
他另一只手的刀抵住了吴阿奶干瘪的胸膛,刀尖开始往里送。
就在这时候从吴阿奶身后伸出来一只手,修长,干净,指甲缝里一点儿泥土都没有,和印象之中的农村人的手完全不一样。
这只手从吴阿奶的脖子旁边伸过来,贴在持刀人的脸上,然后。。。。。。往墙上一按。
砰地一声,脑壳直接爆开。
吴阿奶掉下来的那一刻被一只手接住,像是接住顽皮爬墙的小孩子一样把吴阿奶抱在怀里。
来的人是个很高还有些瘦削的年轻人,有一张干干净净的脸,皮肤白的像是女人,长的也有些像女人,眼睛稍显细长,单眼皮,嘴唇很薄。
“三奎!”
吴阿奶看到这个年轻人的脸就喊起来:“快跑!”
三奎不跑,他把吴阿奶轻轻放下来:“送阿奶回屋。”
他身后有个比他稍微矮一些的年轻人,和他相比粗且黑壮,抱起阿奶进院去了,像是哄着要睡着的孩子一样轻轻拍着阿奶的后背。
“阿奶不怕,不怕。”
三奎等阿奶进院之后,眼神阴冷的如同蛇一样扫过那些外来客。
下一息,一把杀猪刀戳进面前刀客的脖子里,快进快出,快到血都没来得及往外喷。
那些刀客看到这一幕全都有些惊讶,他们没想到这样一个看起来朴实无华的村民会如此凶狠。
第二刀是脖子,第三刀是脖子,第四刀第五刀第六刀,刀刀都是刺进脖腔。
快,准,狠,干脆利索,刀刀致命。
最主要的是,这个叫三奎的年轻人自始至终都面无表情,那张白净的像是读书人的脸上,无悲无喜。
只是简单的,精准的,杀人。
那些训练有素也自认为杀人如麻的刀客怕了,他们成群结队浩浩荡荡而来,进村的时候还在说着看谁杀的多些,杀的最少的那个要请喝酒。
他们逃的时候还是成群结队但散乱的像是被狼追赶的羊,他们忘了手里的刀也能杀人,就如同羊忘了头顶的角也能殊死一搏。
有人慌不择路跑进一条小路上,迎面过来一个拿着镰刀的村民,穿着补丁套补丁的衣服,裤腿已经挽到了膝盖处,小腿上满是泥巴,光着脚走路而来。
下一息,这个刀客就被那把镰刀割掉头颅,拎着头颅的农夫就和拎着一把猪草一样,朴素的像是本该见血就晕的老实人。
更多的刀客逃到了村口,他们是从村西进来的,来之前特意看了看那个泥塑的像,还有人朝泥像啐了口吐沫。
村口就在眼前的时候他们才现那只是入口,不是出口。
七八个村民已经站在那里等着了,有的拿着锄头,有的拿着镰刀,还有拿着粪叉的,高高矮矮各不相同,如果非要找相似,那就是衣服全都有很多补丁。
无事村的人朴素是传统,叶阿爷说过糟蹋任何东西都可能会被山神惩治。
但朴素从来都不是无事村唯一的传统,甚至不是无事村最大的传统。
无事村最大的传统是。。。。。。无事。
大概半个时辰之后,三奎和许多朴素的村民一样,在满地的尸体之中低着头仔细的检查,查看谁还舍不得离开无事村。
送客,要送的周全彻底。
一个刀客仰躺着,嘴里还在溢血,可他却不得不大口大口急促的吸气,因为他觉得唯有这样才能活下去。
那个抱着吴阿奶回院的黑壮小子在这刀客身边蹲下来,伸手扶合了刀客的眼睛,像刚才安慰吴阿奶那样安慰:“不怕不怕。”
然后用手里的捣药锤一下一下敲击在刀客的额头上,直到刀客的额头上多了一个和捣药锤特别契合的坑。
等到确定所有刀客都死了之后,这些朴素的村民拎着脚踝把尸体一具一具的拖到村子外边去。
三奎来回几趟拖着尸体到河边,大奎爹他们这些上了年纪的已经在河边挖出来好大一个坑。
大奎娘也在,怀里搂着七奎,手捂着七奎的眼睛不让他看,七奎就从指间缝隙里看。
三奎把尸体随手扔进坑里:“爹,娘,我得出村一趟,去一下那个叫长安的大村,大奎二奎应该是没争气,姜头怕是被欺负了。”
奎爹奎娘同时点了点头,奎娘说:“去吧,看看姜头和阿爷,你大哥二哥没争气,替我抽他们。”
奎爹说:“如果姜头在外边受委屈,问他要不要回来,要回来你就一起回,他不回你也别回。”
epzbsp;;8ox。netbsp;;;3jx。netbsp;8pzbsp;;;hmbsp;7netb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