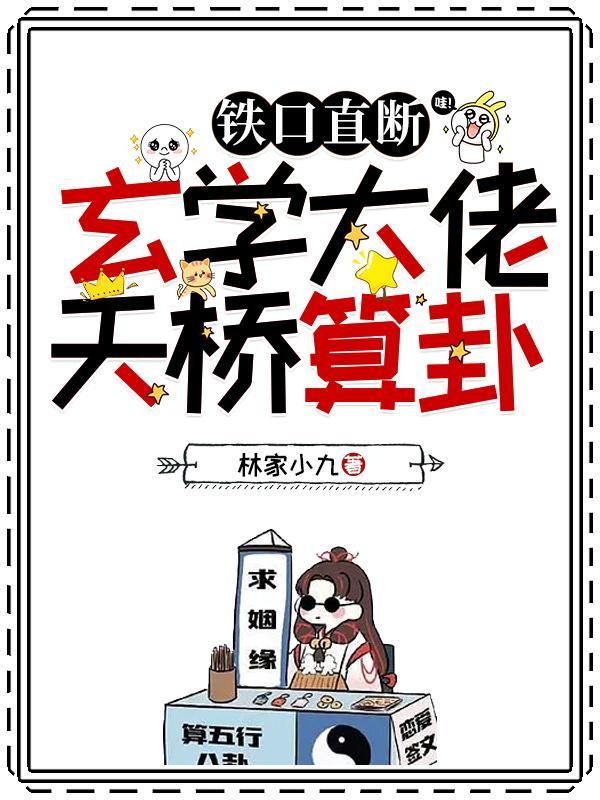笔趣小说>感情破裂之后才发现对方很阴险 > 第22頁(第1页)
第22頁(第1页)
不一會兒他就收起手機,不太自在的扶了扶帽檐,然後隨著一聲輕快的『阿夕』聲後看向這邊,然後慢慢露出了一抹無可奈何的笑。
那是鍾從舟時隔三年來第一次正視林夕的臉和笑容,他還是從前那樣好看,面色紅潤,氣質沉靜內斂,垂手望過來的模樣熟悉的令人眼眶發疼。
鍾從舟怔愣的眨眨眼,感到遲鈍的心臟恢復生機似的開始加跳動起來,他情不自禁的想從拐角處的陰影邁出來,然後像從前那樣牽住他的手。
可有人比他更快了。
他看到個陌生男生一陣風似的跑了過去,笑嘻嘻的問林夕怎麼提前下來了啊,都曬到了,然後遞過去一瓶飲料,伸手為林夕拂開額頭的碎發。
他的穿著幾乎和林夕一模一樣,只除了顏色相反。
鍾從舟知道,在年輕人眼裡那叫情侶裝,他麻木的想著,就像林夕說的那樣,他真的已經往前走了。
鍾從舟被遠遠地落在了身後,自此,黎明,清晨,正午,日落,生命,死亡都與他無關了,他已經被徹底拋棄。
他也在一夕之間懂了,時至今日愛而不舍的人也只能相送。
「也許我也該嘗試走出來了。」鍾從舟這樣告誡著自己,一遍又一遍。可人的情感永遠是最不可控的東西,就算說了再多遍放下他還是會記起林夕,越想擺脫就越深陷其中,越深陷其中就越痛苦。
在不可見底的深淵中,他這台壞掉的機器加的墜落,一點點,一點點,最後終於摔碎在地變成了一堆殘破的,刻滿了『林夕』的零件,再也修復不好了。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鍾從舟不繼續工作了,也直接和外界斷了聯繫,整日獨自待在曾經和林夕共同生活的房子裡,因為林夕回來了。
林夕不生氣了,也對那些傷心事閉口不提,他每天回家都能瞧見他坐在沙發上看書,垂著頭,白皙的指尖按住書的邊緣,粉珍珠一樣。而聽到響動後,他就會抬起頭問鍾從舟:「回來了?」
鍾從舟仿佛做夢一樣,飄飄然不知所向,心房裡被充滿了棉花,軟絨絨的舒服得不得了。他捨不得離開林夕,於是待在家裡像只大型犬一樣圍著他轉。
只是林夕到底還是對他不滿的,時不時的就在他面前板著臉,說我走了,然後就不管鍾從舟如何懇切挽留,驀的變成一團霧氣消散了。
乾乾淨淨的,好似從來沒有出現過。
而鍾從舟別無他法,只能等。
可是沒過多久,這種一心沉迷情情愛愛的行為就激怒了鍾父,他找過來給了他一巴掌,罵他窩囊,沒出息,讓他清醒一下。鍾母則是在一邊捂著臉哭,說當初就不該放縱你去欺騙林夕,她罵他作孽,又抱著他哭說林夕已經走了,這都是他的幻覺,是假的,求他去治病。
鍾從舟呆呆坐著,只在鍾母給林夕打電話,崩潰的求他過來探望一眼時轉了轉眼珠。
「這下真的林夕應該會來了吧。」鍾從舟痴痴地想著,可是電話掛斷後,他等啊等,等啊等,等到太陽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林夕都沒有來。
真的,假的,都沒有來。
「既然他不來,那我就去找他。」鍾從舟渾渾噩噩的想,「我們分手六年了,他會原諒我嗎?」
在這情緒崩裂後的第六年,他終於有勇氣站在最愛的人面前,想在自我懲罰後再求他原諒一次。
「你是……」林夕卻幾乎忘記了他的名字,遲疑的說,「鍾先生?」
三年前在林夕樓下見過的男生就站在他身邊,聞言臉上驚訝的表情立刻轉變成了敵意,他像個護崽兒的老母雞似的上前半步把林夕擋在身後,然後上下打量鍾從舟。
常年的病痛讓鍾從舟受盡折磨,往日裡高大健壯的身體變的骨瘦如柴,西裝掛在身上,風一吹都空蕩蕩的,他的臉也不像從前英俊了,蒼白瘦削,仿佛多年的癮君子。
這幅模樣是比不上那個男生的,對方嫌棄的撇了撇嘴,鬆口氣似的嘟囔了句也不怎麼樣嘛。
「……」林夕瞪了那男生一眼,轉過來歉意的對鍾從舟笑笑,「抱歉,他不太懂事。」儼然是一副回護的姿態。
鍾從舟張了張嘴,就又聽林夕說了再見。
他們攜著手來,又攜著手離開了,鍾從舟甚至都沒有來得及和林夕說上一句話。
他望著那雙人影,恍惚間靈魂早已出竅附在那男生身上,說笑著同林夕離開了。而被遺留在原地的鐘從舟也不過只是具空空的軀殼罷了。
軀殼看向馬路上的車輛,想他大概永遠也不能擁有林夕了,他完全出局了,就像多年前他問過的林夕的問題。
「如果我在感情上背叛了你,我們會分手嗎?」
「會。」
「那我該怎麼求得你的原諒呢?」
「死亡吧。」林夕在書上塗塗畫畫的,漫不經心的回答,「如果我們結束了,那只有死亡才是交叉點,因為死亡能把一切事情清零,那時候我們就兩清了。」
說完他自己先笑了:「我說的好中二哦。」
死亡,鍾從舟想,如果我用生命贖了罪,在奈何橋等到林夕時,能不能聽他重笑著叫一聲從舟呢?
林夕會原諒他嗎?
鍾從舟回到家的時候,鍾母還在痛哭,用碎掉的語氣求他振作,他只能答應她會吃藥,會睡覺,會吃飯,也像他們期待的那樣走出屋子,身體一天天恢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