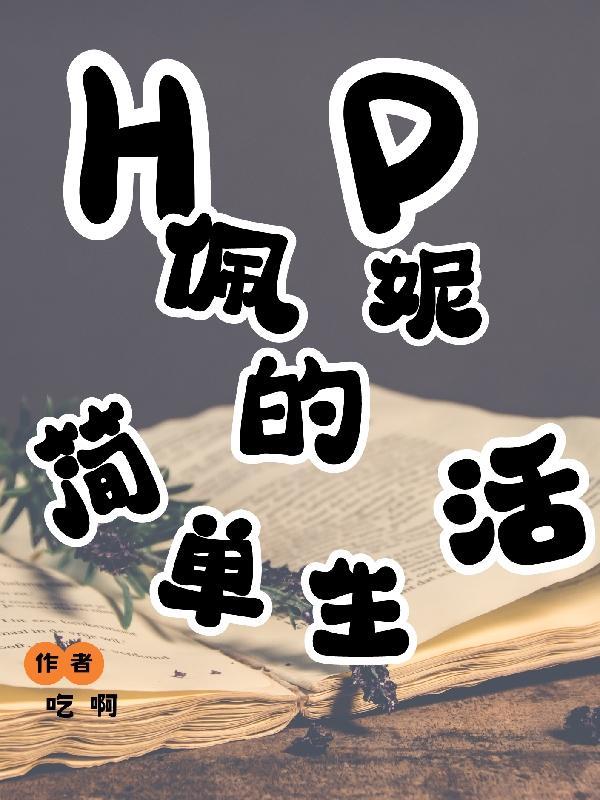笔趣小说>白璧有瑕作文 > 第20章 谁的灵魂如何安慰(第1页)
第20章 谁的灵魂如何安慰(第1页)
课程都已经学完了,剩下的就是枯燥的复习,得亏了大家心态好,偶尔还能苦中作乐。
说起来现在就业前景堪忧,白璧微灵机一动:“咱们四个,加上梁鸿飞他们宿舍四个,八个人学不同专业,到时候联手办医院怎么样?”
这么想当然的主意,也只有她天马行空的脑洞配得上了吧。桑兰雪率先开口了:“没资金!”
白璧微:“贷!”
陈雨然:“没器材!”
白璧微:“买!”
衣竹:“没护士!”
白璧微:“请!”
桑兰雪:“没病号!”
白璧微一把抓过陈雨然来:“扮!”
大家直接笑疯了,却是谁也没有理会她的馊主意。白璧微不死心地打电话找梁鸿飞商量,得到的当然也是拒绝,还有毫不留情的嘲笑。
怎么都领会不到她的良苦用心呢……白璧微无可奈何,只得大声哀号:“我以我血荐轩辕,双袖龙钟泪不干。嫦娥孤栖与谁邻?四万万神州竟无人!”
陈雨然又是好笑又是好气:“你在七拉八扯什么呢?”
白璧微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衣竹冷冷地补了一句:“还用问吗?她什么时候正常过?”
桑兰雪跟着补刀:“她经常神经搭错线,咱们早该习惯了呀。”
白璧微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拉开宿舍门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
这个破地儿是一天也没法待了!
*****
第二天下午放学后,白璧微出去寄了封信,回到宿舍时天色已经暗了。室友们各自在看书,白璧微也悄无声息地回到自己的位置,拿本书专心致志苦读起来。
过了很久,估计是看累了,衣竹从解剖课本上抬起头来,揉了揉眼睛问桑兰雪:“在看什么?”
桑兰雪无奈地扬扬课本:“亲爱的马克思同志的理论。”转眼看见白璧微拿着本楚辞呆,有些奇怪道:“怎么还不好好看书?想什么呢?”
白璧微回过神来,笑了一笑:“怀念伟大的屈原老先生呗。”
“现在?端午节早过了……”桑兰雪小声嘀咕。
“就是现在才怀念啊。”白璧微瞥了一眼马克思理论课本,“我现还是中国人疼中国人,德国人给咱们安排了这么大一门必修课,看看屈原多好,还给几天假期。”
衣竹和桑兰雪都是一头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汗――敢情在这位同学眼里,屈原最大的贡献就是拼了老命为后人换来三天假?
那位老先生泉下有知,估计得哭得很伤心啊。
*****
白璧微笑了一会儿,现宿舍里就她们三个人,便问:“然然呢?”
桑兰雪回答:“好像是去一家画馆?说是刚要开业,她去帮帮忙。”
白璧微随即明白了。宁无踪要在这儿开一座画馆,从此一直守着陈雨然,再不离开。
有些欣喜。她相信自己不会看错,宁无踪对陈雨然是真心的。
却也有些忧虑。宁无踪的身份不可能是普通的画师,以后……会不会影响到陈雨然原本平静的生活?
却也无法多说、多做什么。
各人有各人的际遇,各人有各人的造化,希望他们一切都好。
淋过雨的人,大抵有两种心态。一种是希望借给别人一把伞,让人免遭淋雨之苦;另一种则是把别人的伞撕破,让其同自己一般,淋湿,滑倒,一身狼狈。
白璧微无疑是前者。不论自己遭遇如何,她始终是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可以平安幸福,无忧无虑。
两位室友都各自好好看书了,白璧微抽出日记,缓缓写下几行字。
草原上有一个传说,如果有人甘愿用心尖上的血染红流浪者的剑,那么他的灵魂就会得到安慰,不会再漂泊无依。
放下笔凝神沉思了片刻,白璧微轻轻叹了口气。
宁无踪和陈雨然的心,都曾经流浪了许多年,可是,因为那份浓浓的爱意,他们终于相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不会再流浪了。
可是她自己,却为何无法唤回那个人?她是多么希望他能够不再漂泊,安定下来……
如果,如果可以与他重逢,她情愿用自己心尖上的血,来染红他的剑。
只求他的灵魂可以安宁下来,永远不再流浪。
长出口气,将所有的伤痛轻轻折叠收好――既然没有人为她遮挡那许多的凄风苦雨,她就要学着好好保护自己,为自己的心构筑一个坚固的甲壳,就算内心深处,习惯冰冷,习惯隐藏自己。